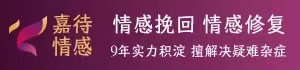作者:Bérénice Reynaud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Senses of Cinema(201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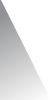 随着小型、轻便的录音和剪辑设备在中国大陆的风行,纪录片创作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局限于北京,也不仅局限于艺术圈。曾经的「新纪录片运动」的范围越走越宽,无论是遥远省份的农民、打破常规的视觉艺术家,还是以摄影机为武器的活动家都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一些新的、与直接电影不同的拍法开始显现。这篇文章此前已经发表在了本刊上,此次更新了文中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细节和评论信息。直到8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纪录片」都是由国家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这些专题片严格遵循既定的规则——将画面与事先写好的旁白相匹配。随后,在吴文光、段锦川、李红和蒋樾的作品中,已经开始有了「真实电影」的影子,开始了新的纪录片实验。九十年代,更自由的经济体制开始施行。「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开始出现。许多像吴文光(《流浪北京》,1990)和王兵(《铁西区》,2003)这样的导演为这股纪录片的新浪潮奠定了基础,使得纪录片不再从属于专题片。然而,电视专题片仍然是许多日后成为独立导演的年轻人的训练场,例如马莉、高子鹏和徐童。李玉曾为央视拍摄了几部纪录片,例如曾遭遇麻烦的《姐姐》(1996)。她转而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今年夏天》(2001),这部充满纪实风格的影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用带有同情的视角描述了北京一对女同性恋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保护她的拍摄对象,李明远从纪录片转到了故事片的创作。对于那些坚持拍摄纪录片的媒介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演变是从一件拍摄设备开始的。吴文光在香港购买了一台数码摄影机,用它拍摄了《江湖》(2000),讲述了一个歌舞团的故事之后许多导演都开始效仿这种拍法。正如概念艺术家、电影制片人和出版商欧宁所指出的,「这种小型、对用户友好、低成本的摄影机很快就成为艺术家们最喜欢的媒介......而笔记本电脑剪辑软件的普及催生了独立电影和视频艺术的繁荣。」互联网的繁荣和DVD的扩散,无论盗版与否,都「打破了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隔离和信息空白,打破了学术界的文化垄断和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并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民主』时代。」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大栅栏》(2006)中,欧宁测试了这种「视觉民主」的限度,他和艺术家曹斐共同创作了这部作品,将焦点对准了北京大栅栏社区的居民。这同时也是一项对2008年奥运会之前正在被拆除的社区的社会性研究。它结合了印刷品、照片、网站和展览等多种媒介形式,构成了所谓的「另类城市档案」。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欧宁和曹斐将摄影机交给了张金利——一位餐馆老板和社区活动家,继而拍出了《煤市街》(2006),记录了城市发展过程中拆迁政策造成的破坏。但是,在张金利自己的房子被摧毁的那一刻,他被禁止拍摄,只能流泪注视着这一切。《煤市街》大部分镜头确实是由张金利拍摄的,反过来,他也成了「专业」制作团队(欧宁、曹斐作为导演,黄伟凯任摄影)所拍摄的废墟景观中的一个人物——这种结构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作者」的意味,且带有窥视、同情和无力感。在《前门前》中,导演奥利维耶·梅斯和张亚璇聚焦于北京另一个社区受到的破坏。他们走访了那些拒绝搬迁的「钉子户」,当推土机铲平了他们的房子后,他们在废墟中继续生活;他们见证了那些回到他们的房子曾经存在的地方的人们的悲痛、愤怒和无助。王清仁的《博弈》(2010)历时数年拍摄,记录了两个小村庄决心抵制为修建高速公路和工厂而进行的拆迁所进行的「游戏」。由于补偿款太少,因拆迁而无家可归的村民决定建造非法建筑,而这些建筑本身也会被拆毁,他们提出了诉讼,法庭审理,并涉嫌腐败。关于城市破坏的最原始的作品是丛峰的第四部长片《地层1:来客》(2012),这同样是一部混合了虚构和纪实元素的影片,其两部分相互映照的叙事结构令人瞩目。在A部分,两个人在一栋废弃的建筑里相遇,分享他们过去生活的记忆。在B部分,他们回到了现在正被推土机摧毁的地方。正如丛峰所解释的,「地层」指的是「不再存在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它以不同层次的城市景观堆积在一起。废墟、瓦砾和破坏是如此普遍的现实,以至于它们总是出现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作者的作品中。在《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2007)中,崔子恩将镜头转向一群生活在北京郊区棚户区的农民工子女,并跟踪报道了源海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在被房东锁住后继续上课、斗争的过程。孩子们在拆迁现场学习、吃饭和玩耍。2001年,将同性恋称为精神疾病的「医学」裁决被废除,这为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变性人题材或变装表演者的独立电影开辟了道路。2001年对于同性恋文化来说确实是一个喜人的年份。《今年夏天》在威尼斯获奖,这开启了石头的职业生涯,她接着拍摄了许多纪录片,如《女人50分钟》(2006)。第一部关于女同性恋夫妇的纪录片,英未未的《盒子》也于2001年完成。早在2000年,第六代电影人张元就导演了《金星小姐》,这是一副关于著名舞蹈家/编舞家金星的肖像,她在1996年决定成为一名女性,影片中包括了她进行变性手术的镜头。张涵子的《唐唐的故事》(2004)讲述了属于北京一位变装表演者的美妙夜晚(亮片、假发、羽毛、高跟鞋、化妆、闪亮的演出服)、灰色的早晨和跨性别的爱情故事。在《人面桃花》(2005)中,杜海滨用分屏的形式展现了三个在成都表演的变装皇后的「分裂生活」。视觉艺术家邱炯炯的第四部纪录片《姑奶奶》(2010年),是对跨性别表演者「碧浪达夫人」的充满爱意和优雅的描写。(译者注:孟京辉的戏剧《柔软》同样以碧浪达为原型。)变装皇后文化也启发了范坡坡的《舞娘》(2011)。范坡坡生于1985年,他最著名的电影《柜族》(2010)采访了数位面临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出柜(或不出柜)的年轻人。在压力下结婚的男同性恋者比例很高,这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影片倾听了那些被困在这种矛盾中的人的故事和困境。它的姊妹片《彩虹伴我心》(2012)则以同情的态度为那些违背「社会规范」,接受自己孩子的同性恋的父母提供了发言的机会。与崔子恩共同创办北京同性恋电影节的杨洋,虽然承认自己的异性恋身份,但她对同性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从策展人、学者和组织者转而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并拍摄了电影《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儿影展十年游击战》(2011)。《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儿影展十年游击战》(2011)尽管中国人表达私人情感的方式是内敛的,但「私影像」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影片都对导演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导演的身体、声音,无论是在画面还是背景音中的缺席/出现,都成为了片中的重要元素。杨荔钠的《老头》(1999)通过鲜活的纪实影像和日记般的叙述,优雅地将自己的声音嵌入到了影片的纹理中。在《老安》(2008)中,杨荔钠讲述了在公园里跳舞的老人的黄昏恋故事。在同年的另一部影片《我的邻居说鬼子》,她和年长的邻居谈起了他们对抗日战争的回忆。在《野草》(2009)中,她讲述了一位被遗弃在孤儿院小男孩的故事,跟拍了12年。对这些拍摄对象来说,她是知己,是朋友,有时也是被调戏的对象,她的建议时而被采纳时而被拒绝,不过没有人能否认她的存在。2005年,吴文光(《流浪北京》)发起了「中国乡村自治电影计划」,他培训农民使用数码相机记录他们村里组织的第一次地方选举。同年,他和他的合作者,现代舞编导文慧,在北京东北郊区开设了一个舞蹈和电影制作工作室兼录像档案馆,名为草场地工作室。在这里实习的村民和学习电影扥人被鼓励制作关于他们当地社区的个人作品,有些人将摄影机视为他们身体的延伸。吴文光创造了「私人语言纪录片」的概念,他将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片段剪辑成《操他妈的电影》(2005),对电影业中的「掌权者」和「局外人」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进行了辛辣的探索:一个无家可归的农民王诛天试图兜售他的自传剧本;年轻的外地女孩正为一个妓女的角色进行试镜;以及被警察追捕的销售盗版DVD的小贩小吴。吴文光将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小吴最终逃脱了镜头的注视,消失在人群中。这些女演员的身体被窥视着——这是电视摄制组无意识的残酷行为的一种暗示。影片的核心是王诛天和导演吴文光之间的关系,王诛天是个无名小卒,有着发自内心的妄想,而吴则是一个著名的导演。《操他妈的电影》中,吴文光并没有过多地介入。而在《治疗》(2011)中,他将自己对母亲去世的悲痛升华为对记忆的本质、时间的流逝、失去的创伤的探讨,以及帮助我们记忆的工具,例如写作和记录影像。在与文慧合作多媒体表演项目「记忆计划」的同时,吴文光海鼓励他的学生通过采访他们的祖父母和村里的长者来构成一个私人档案,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些影片中最成功的是由邹雪平导演的《饥饿的村子》(2010)、《吃饱的村子》(2011)、《孩子的村子》(2012)和《垃圾的村子》(2013)。与此同时,文慧在为演出而挖掘其家族历史的秘密时,发现了一个一直被她忽略的大姨妈,她找到了她,并在《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2011)中通过叙述和表演,为这位女性精心打造了一幅动人的肖像。 自张元的《妈妈》(1990)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以及贾樟柯的《小武》(1998)以来,当代中国电影一直在虚构和纪实之间游走。2001年,贾樟柯完成了一部半小时的观察性纪录片《公共场所》,这启发他拍了长片《任逍遥》(2002)。刘小东是《冬春的日子》的主人公,也是第六代电影人的长期朋友和合作者,他邀请贾樟柯拍摄他在三峡地区为拆迁工人绘画的过程。
随着小型、轻便的录音和剪辑设备在中国大陆的风行,纪录片创作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局限于北京,也不仅局限于艺术圈。曾经的「新纪录片运动」的范围越走越宽,无论是遥远省份的农民、打破常规的视觉艺术家,还是以摄影机为武器的活动家都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一些新的、与直接电影不同的拍法开始显现。这篇文章此前已经发表在了本刊上,此次更新了文中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细节和评论信息。直到8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纪录片」都是由国家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这些专题片严格遵循既定的规则——将画面与事先写好的旁白相匹配。随后,在吴文光、段锦川、李红和蒋樾的作品中,已经开始有了「真实电影」的影子,开始了新的纪录片实验。九十年代,更自由的经济体制开始施行。「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开始出现。许多像吴文光(《流浪北京》,1990)和王兵(《铁西区》,2003)这样的导演为这股纪录片的新浪潮奠定了基础,使得纪录片不再从属于专题片。然而,电视专题片仍然是许多日后成为独立导演的年轻人的训练场,例如马莉、高子鹏和徐童。李玉曾为央视拍摄了几部纪录片,例如曾遭遇麻烦的《姐姐》(1996)。她转而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今年夏天》(2001),这部充满纪实风格的影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用带有同情的视角描述了北京一对女同性恋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保护她的拍摄对象,李明远从纪录片转到了故事片的创作。对于那些坚持拍摄纪录片的媒介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演变是从一件拍摄设备开始的。吴文光在香港购买了一台数码摄影机,用它拍摄了《江湖》(2000),讲述了一个歌舞团的故事之后许多导演都开始效仿这种拍法。正如概念艺术家、电影制片人和出版商欧宁所指出的,「这种小型、对用户友好、低成本的摄影机很快就成为艺术家们最喜欢的媒介......而笔记本电脑剪辑软件的普及催生了独立电影和视频艺术的繁荣。」互联网的繁荣和DVD的扩散,无论盗版与否,都「打破了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隔离和信息空白,打破了学术界的文化垄断和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并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民主』时代。」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大栅栏》(2006)中,欧宁测试了这种「视觉民主」的限度,他和艺术家曹斐共同创作了这部作品,将焦点对准了北京大栅栏社区的居民。这同时也是一项对2008年奥运会之前正在被拆除的社区的社会性研究。它结合了印刷品、照片、网站和展览等多种媒介形式,构成了所谓的「另类城市档案」。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欧宁和曹斐将摄影机交给了张金利——一位餐馆老板和社区活动家,继而拍出了《煤市街》(2006),记录了城市发展过程中拆迁政策造成的破坏。但是,在张金利自己的房子被摧毁的那一刻,他被禁止拍摄,只能流泪注视着这一切。《煤市街》大部分镜头确实是由张金利拍摄的,反过来,他也成了「专业」制作团队(欧宁、曹斐作为导演,黄伟凯任摄影)所拍摄的废墟景观中的一个人物——这种结构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作者」的意味,且带有窥视、同情和无力感。在《前门前》中,导演奥利维耶·梅斯和张亚璇聚焦于北京另一个社区受到的破坏。他们走访了那些拒绝搬迁的「钉子户」,当推土机铲平了他们的房子后,他们在废墟中继续生活;他们见证了那些回到他们的房子曾经存在的地方的人们的悲痛、愤怒和无助。王清仁的《博弈》(2010)历时数年拍摄,记录了两个小村庄决心抵制为修建高速公路和工厂而进行的拆迁所进行的「游戏」。由于补偿款太少,因拆迁而无家可归的村民决定建造非法建筑,而这些建筑本身也会被拆毁,他们提出了诉讼,法庭审理,并涉嫌腐败。关于城市破坏的最原始的作品是丛峰的第四部长片《地层1:来客》(2012),这同样是一部混合了虚构和纪实元素的影片,其两部分相互映照的叙事结构令人瞩目。在A部分,两个人在一栋废弃的建筑里相遇,分享他们过去生活的记忆。在B部分,他们回到了现在正被推土机摧毁的地方。正如丛峰所解释的,「地层」指的是「不再存在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它以不同层次的城市景观堆积在一起。废墟、瓦砾和破坏是如此普遍的现实,以至于它们总是出现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作者的作品中。在《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2007)中,崔子恩将镜头转向一群生活在北京郊区棚户区的农民工子女,并跟踪报道了源海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在被房东锁住后继续上课、斗争的过程。孩子们在拆迁现场学习、吃饭和玩耍。2001年,将同性恋称为精神疾病的「医学」裁决被废除,这为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变性人题材或变装表演者的独立电影开辟了道路。2001年对于同性恋文化来说确实是一个喜人的年份。《今年夏天》在威尼斯获奖,这开启了石头的职业生涯,她接着拍摄了许多纪录片,如《女人50分钟》(2006)。第一部关于女同性恋夫妇的纪录片,英未未的《盒子》也于2001年完成。早在2000年,第六代电影人张元就导演了《金星小姐》,这是一副关于著名舞蹈家/编舞家金星的肖像,她在1996年决定成为一名女性,影片中包括了她进行变性手术的镜头。张涵子的《唐唐的故事》(2004)讲述了属于北京一位变装表演者的美妙夜晚(亮片、假发、羽毛、高跟鞋、化妆、闪亮的演出服)、灰色的早晨和跨性别的爱情故事。在《人面桃花》(2005)中,杜海滨用分屏的形式展现了三个在成都表演的变装皇后的「分裂生活」。视觉艺术家邱炯炯的第四部纪录片《姑奶奶》(2010年),是对跨性别表演者「碧浪达夫人」的充满爱意和优雅的描写。(译者注:孟京辉的戏剧《柔软》同样以碧浪达为原型。)变装皇后文化也启发了范坡坡的《舞娘》(2011)。范坡坡生于1985年,他最著名的电影《柜族》(2010)采访了数位面临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出柜(或不出柜)的年轻人。在压力下结婚的男同性恋者比例很高,这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影片倾听了那些被困在这种矛盾中的人的故事和困境。它的姊妹片《彩虹伴我心》(2012)则以同情的态度为那些违背「社会规范」,接受自己孩子的同性恋的父母提供了发言的机会。与崔子恩共同创办北京同性恋电影节的杨洋,虽然承认自己的异性恋身份,但她对同性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从策展人、学者和组织者转而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并拍摄了电影《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儿影展十年游击战》(2011)。《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儿影展十年游击战》(2011)尽管中国人表达私人情感的方式是内敛的,但「私影像」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影片都对导演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导演的身体、声音,无论是在画面还是背景音中的缺席/出现,都成为了片中的重要元素。杨荔钠的《老头》(1999)通过鲜活的纪实影像和日记般的叙述,优雅地将自己的声音嵌入到了影片的纹理中。在《老安》(2008)中,杨荔钠讲述了在公园里跳舞的老人的黄昏恋故事。在同年的另一部影片《我的邻居说鬼子》,她和年长的邻居谈起了他们对抗日战争的回忆。在《野草》(2009)中,她讲述了一位被遗弃在孤儿院小男孩的故事,跟拍了12年。对这些拍摄对象来说,她是知己,是朋友,有时也是被调戏的对象,她的建议时而被采纳时而被拒绝,不过没有人能否认她的存在。2005年,吴文光(《流浪北京》)发起了「中国乡村自治电影计划」,他培训农民使用数码相机记录他们村里组织的第一次地方选举。同年,他和他的合作者,现代舞编导文慧,在北京东北郊区开设了一个舞蹈和电影制作工作室兼录像档案馆,名为草场地工作室。在这里实习的村民和学习电影扥人被鼓励制作关于他们当地社区的个人作品,有些人将摄影机视为他们身体的延伸。吴文光创造了「私人语言纪录片」的概念,他将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片段剪辑成《操他妈的电影》(2005),对电影业中的「掌权者」和「局外人」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进行了辛辣的探索:一个无家可归的农民王诛天试图兜售他的自传剧本;年轻的外地女孩正为一个妓女的角色进行试镜;以及被警察追捕的销售盗版DVD的小贩小吴。吴文光将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小吴最终逃脱了镜头的注视,消失在人群中。这些女演员的身体被窥视着——这是电视摄制组无意识的残酷行为的一种暗示。影片的核心是王诛天和导演吴文光之间的关系,王诛天是个无名小卒,有着发自内心的妄想,而吴则是一个著名的导演。《操他妈的电影》中,吴文光并没有过多地介入。而在《治疗》(2011)中,他将自己对母亲去世的悲痛升华为对记忆的本质、时间的流逝、失去的创伤的探讨,以及帮助我们记忆的工具,例如写作和记录影像。在与文慧合作多媒体表演项目「记忆计划」的同时,吴文光海鼓励他的学生通过采访他们的祖父母和村里的长者来构成一个私人档案,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些影片中最成功的是由邹雪平导演的《饥饿的村子》(2010)、《吃饱的村子》(2011)、《孩子的村子》(2012)和《垃圾的村子》(2013)。与此同时,文慧在为演出而挖掘其家族历史的秘密时,发现了一个一直被她忽略的大姨妈,她找到了她,并在《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2011)中通过叙述和表演,为这位女性精心打造了一幅动人的肖像。 自张元的《妈妈》(1990)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以及贾樟柯的《小武》(1998)以来,当代中国电影一直在虚构和纪实之间游走。2001年,贾樟柯完成了一部半小时的观察性纪录片《公共场所》,这启发他拍了长片《任逍遥》(2002)。刘小东是《冬春的日子》的主人公,也是第六代电影人的长期朋友和合作者,他邀请贾樟柯拍摄他在三峡地区为拆迁工人绘画的过程。
在拍摄纪录片《东》(2006)的过程中,贾樟柯构思了《三峡好人》(2006)的情节,其中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饰)和一个护士沈红(赵涛)来到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奉节,寻找他们失散的妻子/丈夫。韩三明是贾樟柯的表弟,他在贾樟柯的早期作品中出现,他在《三峡好人》中扮演的是虚构的自己。 他还出现在了贾樟柯2007年的纪录片《无用》中,「淡化」了这部作品的虚构色彩。 《二十四城记》(2008)更进一步,混合了对扮演工人的演员的采访和对真实工人的采访,以往作为军工厂的「420工厂」如今将要变成一个豪华公寓楼 「24城」。在《海上传奇》(2010)中,贾樟柯的叙事在当代上海的影像和这个城市所激发的虚构故事之间展开。 在电影中混合纪录片和虚构元素的电影还包括唐晓白的《完美生活》(2008)和应亮的《另一半》(2006)、短片《慰问》(2009)和《我还有话想说》(2012年)。相反,一些纪录片导演,例如杨蕊,则偏向于虚构性的故事。她的第一部电影《毕摩纪》(2006)展示了将那些「细微的时刻」搬上银幕的微妙技巧——主人公之间的亲密互动、日常生活的元素、仪式的细节、风景背后安静的诱惑、风吹草动的起伏感。杨蕊和剧组在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部落呆了四年,关注一个即将消失的群体——毕摩宗教领袖,他们有权力召唤灵魂、施放诅咒......或成为地方官员。她完成了对祖先习俗(一位老毕摩回忆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村民拥有奴隶的时代)与市场经济侵袭的问题重叠的多面描述。对于她的第二部长片,一部实验性的叙事片《翻山》(2010),她花了三年时间与缅甸边境附近的佤族人相处,并设计了一个相当松散的故事,影片由当地人出演。旅日导演李缨的作品也长于讨论虚构与记录之间的关系。《2H》(2000)和《蒙娜丽莎》(2007)都使用了重现的方式来深入人物的私人困境——一个退休的国民党将军,一个流亡在外的无子女的艺术家,一个因多年前孩子被偷而陷入情感和法律混乱的家庭。耐心对纪录片拍摄来说十分关键。为了拍摄《秉爱》(2007),冯艳花了十年时间观察一位农村妇女张秉爱,她是一名三峡移民。冯如此说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和张秉爱熟悉起来,我们认识八年后,她才开始向我吐露心扉......当水位不断上涨,淹没她的房子时......所有和艰难生活有关的记忆就像洪水冲破水坝一样汹涌而出。我被卷入了她记忆的浪潮里,迷失了方向。」从秉爱顽固地拒绝接受赔偿金并搬走开始,这幅不同寻常的肖像画开始关注她的生活、她的浪漫和失望、她与丈夫的关系——又一个爱情故事。在《和凤鸣》(2007)中,王兵继续坚持了超长时长的拍摄方式(186分钟),但转而采用了更接近香特尔·阿克曼美学的正面拍摄(请看影片对和凤鸣的声音和故事记录的细致程度),而不是安迪·沃霍尔的拍摄方式(当和凤鸣离开房间时,拍摄继续,但一个意外的镜框变化表明拍摄者并没有走开)。 与实验电影(「过程电影」或迈克尔·斯诺的作品)相呼应,《原油》(2008)作为鹿特丹电影节委托的装置作品,让王兵在美学尝试上更进一步,因为这些镜头(被剪辑成14小时)是用监控摄像机拍摄的。因此,他能够记录石油工人在戈壁沙漠中的劳作,但也有休息、互动和充满友谊的时刻。为了拍摄《三姊妹》(2012),王兵在云南一个海拔3200米的小村庄待了几个月,他无疑要承担健康上的风险。在那里,三个小女孩——英英(10岁)、珍珍(6岁)和芬芬(4岁)被父母留在村子里,由一个没有足够食物给自己家人的阿姨照顾。他们的母亲离开了家,父亲在一个小城镇工作,只能通过长途步行或公交车才能到达。女孩们日复一日地采炭、生火、放羊、在水泵旁洗衣服、做家务。珍珍和芬芬的头发被剪短了,因为她们长了虱子,她们的脚在穿塑料靴时因为不穿袜子而流血,英英总是穿着同样的连帽衫,背后绣着 「可爱的日记」。在他的下一部电影,长达四个小时的《疯爱》(2013)中,王兵与云南省昭通精神病院的病人们生活在一起,有些人在那里被关押了几十年。他们被拘留的原因随着岁月被遗忘,但人们可以猜测,有些人是被他们的家人所害,有些是酗酒,有些是狂躁抑郁症,有些被认为是「过于虔诚」。和《铁西区》一样,王兵在《疯爱》中探讨了被困的个人和废弃的建筑之间的关系。一条狭长的走廊绕过巨大的建筑,通过一边的铁丝网俯瞰一个内院,另一边则通向悲惨的宿舍楼。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病人开始在走廊里奔跑,仿佛精神恍惚。王兵跟在他身后,坚定地、顽强地跑着,把他留在画面内。后来,他陪着一个被放了几天假的病人去拜访了他的家乡。在荒凉的街道上,夜晚,那个人开始疯跑,王兵也跟着他跑,把摄影机对准他的背影,那个人最后还是消失在了黑暗中。王兵再现了他作为「拍摄主体」的姿态——这也是使得《铁西区》如此成功的一大要素。《铁西区》和《疯爱》无疑是两部可以留名电影史的作品。中国纪录片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捕捉」真实,更重要的是暗示真实、基本的模糊性——以及对表现的抵抗。在《飘》(2005)中,黄伟凯将重现和临时拍摄的场景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一名流浪歌手的生活方式,他在街头和地下通道卖唱,经常被警察以「流浪」的罪名骚扰、罚款和逮捕。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他偶尔会和一个吸毒的前女友住在一起,同时无休止地与她争吵。这影片的结尾提到了一个著名的案例:一个年轻人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而被警察殴打致死。在《现实是过去的未来》(2009)中,黄伟凯收集了在广州街头随意拍摄、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然后,他选择了20多个事件,将它们重新处理成带有超现实感、颗粒状黑白的影像,通过剪辑创造出一个万花筒般的视图,展示了广州所有充满活力、喧闹和卑鄙的混乱局面。这里有交通事故、与警察的混战和暴力逮捕,也有关于假币和餐馆卫生条例的激烈争论。一条水管破裂,淹没了一个社区,迫使居民在脏水中踩踏;一个疯子在一条繁忙的主干道上奔跑,猪从卡车上逃脱,在街上游荡。黄伟凯不断地将每个故事的简短片段交织在一起;我们认同的并不是主人公的故事,而是纷杂的城市本身,这是一首「城市交响曲」。从《铁路沿线》(2000)——讲述陕西省铁路边的流浪男孩和年轻人——到他在《一四二八》(2009)中对震后四川的记录,再到他最新的作品《少年·小赵》(2015),杜海滨完成了自我纪录片美学的更新。杜海滨花了几年时间来探索中国年轻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他最终放弃了几十个采访片段,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一个独特的年轻人——赵昶通身上。2010年,杜海滨遇到了少年小赵,当时他只有19岁,穿着一身军装,在山西省平遥的街头高喊爱国口号。杜海滨的镜头记录了小赵从高中到大学的过程,并和他的同学一起花了十天时间,在西藏边境附近的一个贫穷村庄教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学习普通话和算术。当他成为 「拆迁」政策的受害者,房子被推倒,得不到补偿,他生病的祖父也被赶走,他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无疑被摧毁了。在香港举行的全球首映式上,赵昶通与杜海滨一起出现,介绍这部电影,观众看到,他的头巾印有美国国旗的图案。正如张献民指出的那样,21世纪初的独立纪录片一直是「挑战(由)建立完美社会的努力所造成的世界灾难的历史」的一种方式,它通过「真实的人物,更通过人类之间不确定的关系,突出了人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 和以上作品显得有些不一样的是,徐童的作品一直在关注被剥夺权利、未被同化的人群——尤其是关注河北省的东北地区(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和邻近的内蒙古居民的生活。 《麦收》(2008)因其展示了一个善良的乡村女孩牛红苗的双重生活而引起了争议、批评,甚至是公众的抗议,牛红苗回到家里帮助她的父母做收割工作——在北京则是一名性工作者。通过展示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徐童打破了这种工作的隐秘性。另一方面,通过用小型数码摄影机记录她们的行为和对话,在她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是不是把她们置于了危险之中,在本体论层面上,他是不是在剥削她们?在他接下来的作品《算命》(2010)中,徐童偶然发现了一个正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当他在跟踪一个贫穷的流动算命师厉百程的困境时,他遇到了他的一个客户唐小雁,并持续拍摄了她的生活。徐童在他的第三部纪录片《老唐头》(2011)中同样拍摄了她,这部影片似乎是《麦收》的变体:两部影片都讲述了一个性工作者回家看望父亲的故事。不过,由于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份不同,其叙事结构也大不相同。唐小雁做着非法采煤的生意,与她的家人们大吵大闹——他们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她与父亲的关系很复杂,在她为父亲清除耳垢的一个场景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80岁的唐希信是一名退休的铁路工人,他用长篇大论的独白讲述了他所看到和经历的艰难困苦,有时还用老照片来向人们提示。这部影片概述了另一段历史,但有一种明确的愤怒感:我们都被耍了。 唐小雁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她有粗俗、刻薄、大吼大叫的一面,同时也富有魅力。她在画面中强调了自己的存在,抢尽了风头,并对拍摄过程中的占有感变得越来越狡猾。她在《四哥》(2013)中再次出现,该片以清晰的黑白画面揭露了她的一个兄弟如诗如画的犯罪生涯——对社会底层、仪式、言谈举止、肢体语言、挑战、危险——以及无情的压制进行了非批判性的观察。在《挖眼睛》(2014)中,盲人民谣歌手二后生以在内蒙古表演二人台为生。通过歌曲和私人谈话,他不断讲述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他的眼睛是如何被一个与他有过热恋的已婚少妇的兄弟挖去的。唐小雁对这个故事很陌生,但她陪伴着徐童跟随二后生的流浪,并与他的母亲走得很近。正如2011年南京独立电影节举办的研讨会所讨论的那样,徐童的作品代表了近期 「描述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的纪录片的顶点。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明显不同,传播学教授吕新雨说,当时「电影人与他们所拍摄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纪录片讲述的是老百姓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矛盾也随之浮现。杜海滨与四川地震的年轻工人阶级受害者找到了共同点,因为他们有相似的童年,但不得不花数年时间去了解弥漫在年轻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感。周浩的影片中,学校老师承认道,他不了解他的学生是如何思考的。对于那些属于被压迫的少数群体的电影人来说,「斜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同性恋电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目前中国独立电影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女性凝视的可能性,我将留在之后进行讨论。但我想以一部杰出的作品来结束这篇文章,它为纪录和虚构之间的混合性以及将镜头转向自己的可能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杨明明42分钟的短片《女导演》(2012)被称为 「仿纪录片」,这个术语反映了其难以确定形式和内容的特质。当工作前景渺茫时,两个时髦的、满嘴脏话的20多岁的艺术学校毕业生(杨明明和她的同伴郭月)决定拍摄对方的生活。这包括坦率地谈论性,用 「下体」换取物质和情感利益,以及通过讨论她们各自与同一个男人(她们昵称为「矮个」)的亲密关系来测试她们的友谊。「摄影机就像一种武器,」杨明明说。「谁拿着它,谁就掌握了关系中的权力。当然,影片中也有模仿男性凝视的时刻。但我认为这部电影打破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总是能意识到谁在拿着摄影机。」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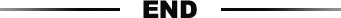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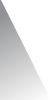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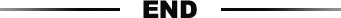







 虹膜
虹膜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