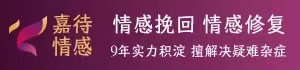作者:Panos Kotzathanasis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Asian Movie Pulse
(2022年5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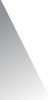 马修·拉克劳是一名法国剪辑师,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他求学于巴黎第三大学,并在2008年获得电影理论硕士学位。2013年,马修凭借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获得金马奖最佳剪辑奖;2017年,他又凭借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获得美国克洛特鲁迪斯独立电影奖最佳剪辑奖。两部电影都入选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注定》还获得了最佳剧本奖。此外,马修参与剪辑的电影还有: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刁亦男导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赵德胤导演的《灼人秘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王晶导演的《不止不休》(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我们与他谈论了在中国剪辑电影的工作历程,与贾樟柯、徐冰、赵德胤等导演以及与制片人和销售代理的合作,还有他的剪辑方法,未来的计划,以及许多其他话题。问:你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了这一行,能先谈谈你成为剪辑师的契机和历程吗?这么多年来你见证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马修: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变了。10年前,我还是个初学者,而在这期间我参与了很多电影。变化最大的是我自己,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有所提升。2008年我刚来到中国时,初始目标是成为一名摄影指导。当时中国电影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每年都有很多电影在拍摄,所以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摄影师、剪辑师和美工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方,我得到了很多剪辑电影的机会。我剪辑的第一部电影是韩杰执导、贾樟柯监制的《Hello!树先生》。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部电影中担任剪辑师,但韩杰给我看了初剪版。在给了他一些意见后,他跟我说:「你来试一试。我给你两周的时间来剪辑一个你的版本。你可以完全自由发挥!」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改变了影片的结构,重新剪辑了很多场景,并增加了一个画外音。后来,贾樟柯和韩杰都非常喜欢我的版本。那是我第一次给剧情片做剪辑,两年后,我剪辑了贾樟柯的《天注定》,该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我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剪辑奖。这为我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同时,我继续与贾樟柯合作了他执导的三部电影以及他监制的多部电影。我觉得目前在中国,很多重要的电影都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制作的——就是40岁左右的人。现在,业内几乎每个人都尊称我为「老师」。虽然我的职业生涯才不过10年,但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手了,这有点不真实!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待在台北。而所有和我合作的导演都在大陆,我不可能飞到北京和他们一起在剪辑室工作。所以我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让我和这些导演一起远程剪辑,同时,它还可以支持高质量的4K画面和5.1声道。我花了几个月的研究和实验,使它得以顺利和安稳地运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投入心血很多的东西,而且我现在一直在使用它。这也使得导演们的工作更容易了:他们只需要一台连接到电视的Mac电脑和稳定的网络。无论他们在世界何处,都可以和我一起进行剪辑,就像我们身处同一个房间一样。今年对于我来说相当特别,因为我参与剪辑了一些非华语电影,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其中包括普蒂邦·阿朗潘的泰国电影《莫里森》;让-夏尔·休在墨西哥拍摄的纪录片《提华纳的脏鸽子》(暂译,The Soiled Doves of Tijuana);阿迪拉·本迪莫拉德和丹米阳联合执导的阿尔及利亚电影《最后的女王》(暂译,The Last Queen)。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导演合作真的很有趣,让我大开眼界。《最后的女王》(暂译,The Last Queen)马修:其实每部电影都是不同的,制作过程也完全不同。有时,导演想更多地介入,频频出现在剪辑室,而有些导演则喜欢给我更多的剪辑自由,然后给我反馈。我努力让自己的工作流程能够适应不同的电影及导演。例如,与泰国导演和阿尔及利亚导演的合作就非常不同。与普蒂邦·阿朗潘合作时,我独自剪辑影片,然后他把意见发回给我,我再做相应的修改。当我们无法通过文字进行沟通时,他会自己做一个粗剪,以表达他的想法,这很有效。至于与阿尔及利亚导演的合作,我们一起剪辑电影,在剪辑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然后,当他们飞回巴黎之后,我们使用我开发的远程剪辑软件一起工作。有趣的是,我今年剪辑的大多数新片都有一个法国(联合)制片人和一个法国国际销售代理。法国的制片人似乎看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他们总是对电影文化有很好的理解。他们真的很关心电影,在剪辑室里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这也让我收获了很多不错的剪辑体验。我总是喜欢接受反馈。马修:贾樟柯人很好,作为剪辑师很容易和他合作。他喜欢经常待在剪辑室,所以我们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通常会处理音效方面的问题,或与不同部门沟通。当他对我们的剪辑感到满意时,他喜欢向其他人展示。例如,我们一起剪辑《江湖儿女》时,就给很多人提前看了片,他们给出了很多不错的反馈。像贾樟柯这样有经验的导演并不害怕别人的反馈,因为他知道如何处理。这绝非易事,因为通常的反馈大概是:「影片很好,我很喜欢,但是......问题1、问题2、问题3、问题4......,」导演和剪辑师有时会有十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尽量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知道剪辑过程要花很多时间,影片需要不断精进。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初剪,而是要改进每个版本,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万事总有一个过程。问:能谈谈《蜻蜓之眼》吗?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几年看过最具独创性的电影之一。马修: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蜻蜓之眼》,因为它对我来说也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电影。在剪辑方面,它打开了我的思路。这是一部只使用监控影像制作而成的电影。在中国,从2015年到2018年,有几个监控摄像头品牌公开播放了所有的视频。制造这些摄像头的公司的网站会全天候直播所有的录像。成千上万的镜头对准了餐馆、寺庙、奶牛场,以及街道和私人公寓。当艺术家兼导演、世界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徐冰看到这一点时,他的团队开始用十台电脑每天24小时记录所有这些录像,整整一年。一年之后,他得到了数千小时的「真实」录像。在录制这些视频的同时,他开始与诗人翟永明一起写剧本。他们从所得到的镜头出发,创作了一个剧情片式的故事。例如,一开始他们录制了很多佛教寺庙的监控画面,所以剧本从一个寺庙开始。通常情况下,对于一部「正常」的电影,你会先写好剧本,然后拍摄和剪辑。这三个部分是完全分开的。虽然你可以在剪辑时改变一点剧本的内容,但通常你不会重新拍摄任何东西。但是对于《蜻蜓之眼》来说,写剧本、拍摄和剪辑都是同时进行的。加入剧组后,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几个小时的随机「真实」录像和一个有两位主角的故事片剧本——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爱情故事。作为剪辑师,我的首要任务是从录像中找到两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主角的人,并与剧本相匹配。因此,当我发现两个人在寺庙里谈话时,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刚好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保留了他们的镜头。然后,我让两个助手根据剧本中的对白进行了录音,我必须把声音放在画面上,并将其与人物的嘴型匹配。当然,对白与画面并不匹配,所以我们不得不重写对白,重新录音,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我们必须根据画面来编写对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花了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尽管这样,我不得不说这一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毕竟我们的素材只有监控录像。一开始,我认为不可能通过这种手法讲述一个故事。但经过两个月的剪辑,我们发现,以我们拥有的长达11000多小时的录像,可以讲述我们想要的任何故事。可能性真的是无限的。马修:是的。徐冰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艺术家,他喜欢尝试很多东西。我们还在电影中嵌入了很多平面设计的东西,因为影片中有一个故事情节,就像电脑开始说话了。在这些场景中,你会看到一些像红框一样的东西围绕着人物和一些信息,如「男人」或「女人」......徐冰希望脸部周围的线条、数字的大小等细节都要完全精确。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和徐冰一起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马修:我不知道,这确实是一次很棒的经验,但徐冰不想再做一部这样的电影了。为一部新片重复同样的概念没有多大意义,至少现在还没有。也许有一天,当技术发生变革,他可能会想再做一部类似的作品。对他来说,有趣的是,通常监控录像是由政府掌控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你不能随意访问它——它不是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的东西。但我们刚好碰到了录像公开的契机。然而,所有播放监控录像的网站后来都关闭了,所以现在无法访问这个巨大的信息库。制作这部影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我并不确定我们最后是否能成功地制作出一部可观赏的、发人深省的作品。我一直在寻找讲故事的新方法,我从不害怕像《蜻蜓之眼》这样的大挑战。马修:赵德胤是一位缅甸导演,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大家庭。他是个好学生,16岁的时候他拿到了台湾的奖学金,并在那里读了高中和大学。毕业后,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台湾,但一直在缅甸拍摄电影。赵德胤的大部分电影都与他自己的生活或他兄弟姐妹的故事有关。我和他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再见瓦城》,讲述了一个缅甸移民去泰国工作的故事。第一次的合作经历很棒:他和我年龄相仿,我们看过的电影也很相似。他对我非常信任,在剪辑过程中我们成了朋友,合作非常顺畅,结果也不错。我们合作的第二部电影是《灼人秘密》,这对他来说是一部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因为这是他在台湾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和女主角吴可熙共同编写的。这部电影的剪辑非常有趣,因为它有时更像一部心理惊悚片,你必须为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考虑整个故事,因为影片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与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不同,我们不想一开始就揭示这个「秘密」,所以观众必须意识到这个女人有问题,但同时也能够理解她。因此在最后,当秘密揭晓时,你会理解她各种行为的动因。这已经很复杂了,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第二次观看影片的观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通常人们在第二次观看影片时,会检查故事的所有细节,看看它们是否有漏洞。那是我第一次剪辑这样的电影,非常刺激。马修:导演给我看了初剪。剧本里有很多情节,叙事相当复杂。而这部电影最初被交给了一位香港的剪辑师,陈序庆,他使得故事的表述更加清晰了。然后,我和导演一起工作了大约两三个星期,以改进结构和表演部分。我差不多是在这个项目的末期才加入的。问:你和导演的合作通常都很顺利吗,还是会时不时发生争执?马修:通常都很顺利。剪辑师的个性往往都相当柔和,因为他们必须平衡自己和导演的个性。而导演的个性一般更加强势,所以我总是非常小心,尽量不去激怒他们。当然,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当我对某件事情有不同意见时,我总是会直言相告。导演拍电影的时候就在现场,所以他们记得整个制作过程。作为一个剪辑师,我看到的是既得的影像,我不关心它是如何完成的。我是第一个观众,当我不喜欢某个东西时,例如镜头质量不好,或者场面调度一般,我总是直接告诉导演。但当我有一个想法,而导演不同意时,我也不会太强求。剪辑过程是漫长的,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目的不是比个水平的高低。你不需要在提出建议的时候让导演同意你的意见,因为也许在剪了一个月后,整个电影的结构完全发生了改变,你的建议可能就显得更有意义。对时间和与你合作的团队抱有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每部影片都有弱点,在剪辑过程中,你要尽量淡化这些弱点(并将优点最大化)。你肯定希望导演能意识到问题,即使有时他/她听到会很痛苦,或你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当影片上映,观众的意见纷纷而至之后,想要再做任何修改就为时已晚了。而作为一个剪辑师,我不希望接到导演绝望的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场景很糟糕,我们没有完全吃透故事的那个部分?」马修:当我去片场时,会在晚餐时见到演员......他们对我通常非常友好,经常开玩笑地说:「请尽可能多地保留我的戏份!」但当真正剪辑电影的时候,我需要把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有时,我们必须剪掉一些演员的戏份。这就是剪辑的现实,虽然这个过程总是很痛苦,但有时是必要的。剪掉一场戏并不总是因为演员的表演。大多数时候,我们剪掉一场戏是因为它是一个次要的故事情节,而且可能会让观众跳脱出主线。作为剪辑师,我很喜欢演员。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脑屏幕后面观察他们。而通常,他们并不认识我。刁亦男导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后,四位主演都拥抱了我。他们非常感谢我所做的工作。那真的是非常感人。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剪辑是一种充满了爱的行为。而在那一次,这种爱得到了回报。马修:他们的处境与导演和剪辑师很不同,因为他们往往在剧本筹备阶段就介入了。因此,他们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知道剧本是如何诞生的,也知道在写作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拍摄过程中不会消失——在剪辑过程中又会再次出现。制片人什么都知道。当然,他们不会每天都在剪辑室,也不会因为每天看8个小时的素材而感到疲倦。因此,当你展示初剪时,制片人的观点对导演和剪辑师都非常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反馈是有人说:「我不明白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很有用的。然后由导演和剪辑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文艺片不会有这种过程,因为导演的愿景和观点是最重要的,而商业片是为了吸引观众,所以会有更多这样的展示或测试,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反馈。对导演来说,展示他的电影,看看人们对它的看法,然后搞清楚他们想看些什么,总是有益的。马修:是的。这是一部素材不多的电影,松太加一开始和一个年轻的剪辑师一起剪辑。他给我看了一个版本,他知道还需要拍摄更多的场景,所以过程有点不同,因为我看到了初剪之后,他问我电影有哪些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我告诉他,结局不是很令人满意,还有一些其他建议。所以两个月后,他重拍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意见对他真的很有用,因为他完全重拍了结局。在他剪辑了新的场景之后,我「润色」了两个星期,只是做了结构上的小调整和节奏的变化。这次经历非常顺畅。问:你会偶尔去到拍摄现场,还是会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马修:在疫情爆发之前,我确实会时不时去片场,但大多数时候,我会待在酒店房间里埋头剪辑。我有时会在拍摄的第一天去。我第一次频繁去片场是拍摄《江湖儿女》的时候,因为这部电影的一部分是用35毫米胶片拍摄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素材送到实验室,实验室扫描后再把它寄给我。要过很多天我才能收到素材,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待在片场。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去片场,但实际上我不去反而更好,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需要观察影像的本质。我不应该知道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例如,我不需要知道拍摄是否因某种原因被推迟,或者导演和演员那天心情不好。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电影制作的信息都是噪音,它可能会扰乱我的工作,或者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客观地看待影像,影响我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疫情爆发之后,我就彻底不去现场了。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素材。我在台湾有一个团队,我和蔡晏珊一起工作。她是台湾人,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大约6年。她一直是我参与的许多电影的合作剪辑师。有时,在拍摄期间,她会做样片的粗剪,有时我来做。有时,她独立剪辑,然后我对她的版本给予反馈,或者我先开始剪辑。有时,我会独自剪辑大部分,最后,如果有需要,她会进行修正。与她合作的好处是,我们非常了解对方,因为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了超过15部电影。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会对镜头感到厌倦,你会失去观看影像和故事的新鲜感。所以比方说,她会先在一部电影上工作一个月,然后我看到它时仍然有新鲜的视角,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问题。反之亦然。在经历了漫长的剪辑过程之后,这很有帮助。我不喜欢那种「这是我的电影,我是剪辑师,其他人不能碰它」的心态。剪辑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它是非常务实的。要么对电影有好处,要么没有。我还有一个合作者,一名助理剪辑师,也在台湾,叫郑翊。由于我今年住在法国,时差恰恰变成了一项优势,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反之亦然。当然还有我的妻子王思静(她是一位制片人),她经常看我们的电影,并给我们提出意见。给她看的时候,我通常很紧张,因为她的批评可能会很尖锐。但是和她一起看总是很有帮助,因为我可以通过第三双眼睛来看待这部电影。马修:嗯,年底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是让-夏尔·休执导的一部电影。目前,我还在剪辑两部中国电影,一部是魏书钧导演的,我还和他合作过《永安镇故事集》。这部电影有点像黑帮片,我很喜欢!他已经拍了三分之二,我在等他完成。另一部是张一白导演的作品,但我还不能透露太多。在我与中国导演合作的同时,我也非常期待剪辑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电影。我不想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做中国电影的法国人」。中国是一个「疯狂」的地方,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有很多拍电影的好基础,有一个很大的电影产业,这非常重要,但我仍然渴望处理新的故事。我喜欢认识新的角色。马修:没有!事实上,我在学生时期确实执导过一些短片,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但自从我成为一名剪辑师后,我就不想再做导演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非常喜欢在不同的项目之间切换,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导演制作一部电影有时需要花两三年,甚至更长。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毅力。对我来说最高的赞誉是,我以前合作过的导演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剪辑他/她的新电影。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现,而信任是导演和剪辑师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将努力继续帮助导演实现他们的愿景。
马修·拉克劳是一名法国剪辑师,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他求学于巴黎第三大学,并在2008年获得电影理论硕士学位。2013年,马修凭借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获得金马奖最佳剪辑奖;2017年,他又凭借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获得美国克洛特鲁迪斯独立电影奖最佳剪辑奖。两部电影都入选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注定》还获得了最佳剧本奖。此外,马修参与剪辑的电影还有: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刁亦男导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赵德胤导演的《灼人秘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王晶导演的《不止不休》(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我们与他谈论了在中国剪辑电影的工作历程,与贾樟柯、徐冰、赵德胤等导演以及与制片人和销售代理的合作,还有他的剪辑方法,未来的计划,以及许多其他话题。问:你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了这一行,能先谈谈你成为剪辑师的契机和历程吗?这么多年来你见证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马修: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变了。10年前,我还是个初学者,而在这期间我参与了很多电影。变化最大的是我自己,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有所提升。2008年我刚来到中国时,初始目标是成为一名摄影指导。当时中国电影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每年都有很多电影在拍摄,所以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摄影师、剪辑师和美工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方,我得到了很多剪辑电影的机会。我剪辑的第一部电影是韩杰执导、贾樟柯监制的《Hello!树先生》。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部电影中担任剪辑师,但韩杰给我看了初剪版。在给了他一些意见后,他跟我说:「你来试一试。我给你两周的时间来剪辑一个你的版本。你可以完全自由发挥!」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改变了影片的结构,重新剪辑了很多场景,并增加了一个画外音。后来,贾樟柯和韩杰都非常喜欢我的版本。那是我第一次给剧情片做剪辑,两年后,我剪辑了贾樟柯的《天注定》,该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我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剪辑奖。这为我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同时,我继续与贾樟柯合作了他执导的三部电影以及他监制的多部电影。我觉得目前在中国,很多重要的电影都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制作的——就是40岁左右的人。现在,业内几乎每个人都尊称我为「老师」。虽然我的职业生涯才不过10年,但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手了,这有点不真实!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待在台北。而所有和我合作的导演都在大陆,我不可能飞到北京和他们一起在剪辑室工作。所以我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让我和这些导演一起远程剪辑,同时,它还可以支持高质量的4K画面和5.1声道。我花了几个月的研究和实验,使它得以顺利和安稳地运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投入心血很多的东西,而且我现在一直在使用它。这也使得导演们的工作更容易了:他们只需要一台连接到电视的Mac电脑和稳定的网络。无论他们在世界何处,都可以和我一起进行剪辑,就像我们身处同一个房间一样。今年对于我来说相当特别,因为我参与剪辑了一些非华语电影,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其中包括普蒂邦·阿朗潘的泰国电影《莫里森》;让-夏尔·休在墨西哥拍摄的纪录片《提华纳的脏鸽子》(暂译,The Soiled Doves of Tijuana);阿迪拉·本迪莫拉德和丹米阳联合执导的阿尔及利亚电影《最后的女王》(暂译,The Last Queen)。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导演合作真的很有趣,让我大开眼界。《最后的女王》(暂译,The Last Queen)马修:其实每部电影都是不同的,制作过程也完全不同。有时,导演想更多地介入,频频出现在剪辑室,而有些导演则喜欢给我更多的剪辑自由,然后给我反馈。我努力让自己的工作流程能够适应不同的电影及导演。例如,与泰国导演和阿尔及利亚导演的合作就非常不同。与普蒂邦·阿朗潘合作时,我独自剪辑影片,然后他把意见发回给我,我再做相应的修改。当我们无法通过文字进行沟通时,他会自己做一个粗剪,以表达他的想法,这很有效。至于与阿尔及利亚导演的合作,我们一起剪辑电影,在剪辑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然后,当他们飞回巴黎之后,我们使用我开发的远程剪辑软件一起工作。有趣的是,我今年剪辑的大多数新片都有一个法国(联合)制片人和一个法国国际销售代理。法国的制片人似乎看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他们总是对电影文化有很好的理解。他们真的很关心电影,在剪辑室里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这也让我收获了很多不错的剪辑体验。我总是喜欢接受反馈。马修:贾樟柯人很好,作为剪辑师很容易和他合作。他喜欢经常待在剪辑室,所以我们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通常会处理音效方面的问题,或与不同部门沟通。当他对我们的剪辑感到满意时,他喜欢向其他人展示。例如,我们一起剪辑《江湖儿女》时,就给很多人提前看了片,他们给出了很多不错的反馈。像贾樟柯这样有经验的导演并不害怕别人的反馈,因为他知道如何处理。这绝非易事,因为通常的反馈大概是:「影片很好,我很喜欢,但是......问题1、问题2、问题3、问题4......,」导演和剪辑师有时会有十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尽量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知道剪辑过程要花很多时间,影片需要不断精进。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初剪,而是要改进每个版本,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万事总有一个过程。问:能谈谈《蜻蜓之眼》吗?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几年看过最具独创性的电影之一。马修: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蜻蜓之眼》,因为它对我来说也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电影。在剪辑方面,它打开了我的思路。这是一部只使用监控影像制作而成的电影。在中国,从2015年到2018年,有几个监控摄像头品牌公开播放了所有的视频。制造这些摄像头的公司的网站会全天候直播所有的录像。成千上万的镜头对准了餐馆、寺庙、奶牛场,以及街道和私人公寓。当艺术家兼导演、世界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徐冰看到这一点时,他的团队开始用十台电脑每天24小时记录所有这些录像,整整一年。一年之后,他得到了数千小时的「真实」录像。在录制这些视频的同时,他开始与诗人翟永明一起写剧本。他们从所得到的镜头出发,创作了一个剧情片式的故事。例如,一开始他们录制了很多佛教寺庙的监控画面,所以剧本从一个寺庙开始。通常情况下,对于一部「正常」的电影,你会先写好剧本,然后拍摄和剪辑。这三个部分是完全分开的。虽然你可以在剪辑时改变一点剧本的内容,但通常你不会重新拍摄任何东西。但是对于《蜻蜓之眼》来说,写剧本、拍摄和剪辑都是同时进行的。加入剧组后,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几个小时的随机「真实」录像和一个有两位主角的故事片剧本——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爱情故事。作为剪辑师,我的首要任务是从录像中找到两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主角的人,并与剧本相匹配。因此,当我发现两个人在寺庙里谈话时,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刚好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保留了他们的镜头。然后,我让两个助手根据剧本中的对白进行了录音,我必须把声音放在画面上,并将其与人物的嘴型匹配。当然,对白与画面并不匹配,所以我们不得不重写对白,重新录音,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我们必须根据画面来编写对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花了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尽管这样,我不得不说这一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毕竟我们的素材只有监控录像。一开始,我认为不可能通过这种手法讲述一个故事。但经过两个月的剪辑,我们发现,以我们拥有的长达11000多小时的录像,可以讲述我们想要的任何故事。可能性真的是无限的。马修:是的。徐冰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艺术家,他喜欢尝试很多东西。我们还在电影中嵌入了很多平面设计的东西,因为影片中有一个故事情节,就像电脑开始说话了。在这些场景中,你会看到一些像红框一样的东西围绕着人物和一些信息,如「男人」或「女人」......徐冰希望脸部周围的线条、数字的大小等细节都要完全精确。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和徐冰一起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马修:我不知道,这确实是一次很棒的经验,但徐冰不想再做一部这样的电影了。为一部新片重复同样的概念没有多大意义,至少现在还没有。也许有一天,当技术发生变革,他可能会想再做一部类似的作品。对他来说,有趣的是,通常监控录像是由政府掌控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你不能随意访问它——它不是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的东西。但我们刚好碰到了录像公开的契机。然而,所有播放监控录像的网站后来都关闭了,所以现在无法访问这个巨大的信息库。制作这部影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我并不确定我们最后是否能成功地制作出一部可观赏的、发人深省的作品。我一直在寻找讲故事的新方法,我从不害怕像《蜻蜓之眼》这样的大挑战。马修:赵德胤是一位缅甸导演,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大家庭。他是个好学生,16岁的时候他拿到了台湾的奖学金,并在那里读了高中和大学。毕业后,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台湾,但一直在缅甸拍摄电影。赵德胤的大部分电影都与他自己的生活或他兄弟姐妹的故事有关。我和他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再见瓦城》,讲述了一个缅甸移民去泰国工作的故事。第一次的合作经历很棒:他和我年龄相仿,我们看过的电影也很相似。他对我非常信任,在剪辑过程中我们成了朋友,合作非常顺畅,结果也不错。我们合作的第二部电影是《灼人秘密》,这对他来说是一部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因为这是他在台湾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和女主角吴可熙共同编写的。这部电影的剪辑非常有趣,因为它有时更像一部心理惊悚片,你必须为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考虑整个故事,因为影片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与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不同,我们不想一开始就揭示这个「秘密」,所以观众必须意识到这个女人有问题,但同时也能够理解她。因此在最后,当秘密揭晓时,你会理解她各种行为的动因。这已经很复杂了,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第二次观看影片的观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通常人们在第二次观看影片时,会检查故事的所有细节,看看它们是否有漏洞。那是我第一次剪辑这样的电影,非常刺激。马修:导演给我看了初剪。剧本里有很多情节,叙事相当复杂。而这部电影最初被交给了一位香港的剪辑师,陈序庆,他使得故事的表述更加清晰了。然后,我和导演一起工作了大约两三个星期,以改进结构和表演部分。我差不多是在这个项目的末期才加入的。问:你和导演的合作通常都很顺利吗,还是会时不时发生争执?马修:通常都很顺利。剪辑师的个性往往都相当柔和,因为他们必须平衡自己和导演的个性。而导演的个性一般更加强势,所以我总是非常小心,尽量不去激怒他们。当然,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当我对某件事情有不同意见时,我总是会直言相告。导演拍电影的时候就在现场,所以他们记得整个制作过程。作为一个剪辑师,我看到的是既得的影像,我不关心它是如何完成的。我是第一个观众,当我不喜欢某个东西时,例如镜头质量不好,或者场面调度一般,我总是直接告诉导演。但当我有一个想法,而导演不同意时,我也不会太强求。剪辑过程是漫长的,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目的不是比个水平的高低。你不需要在提出建议的时候让导演同意你的意见,因为也许在剪了一个月后,整个电影的结构完全发生了改变,你的建议可能就显得更有意义。对时间和与你合作的团队抱有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每部影片都有弱点,在剪辑过程中,你要尽量淡化这些弱点(并将优点最大化)。你肯定希望导演能意识到问题,即使有时他/她听到会很痛苦,或你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当影片上映,观众的意见纷纷而至之后,想要再做任何修改就为时已晚了。而作为一个剪辑师,我不希望接到导演绝望的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场景很糟糕,我们没有完全吃透故事的那个部分?」马修:当我去片场时,会在晚餐时见到演员......他们对我通常非常友好,经常开玩笑地说:「请尽可能多地保留我的戏份!」但当真正剪辑电影的时候,我需要把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有时,我们必须剪掉一些演员的戏份。这就是剪辑的现实,虽然这个过程总是很痛苦,但有时是必要的。剪掉一场戏并不总是因为演员的表演。大多数时候,我们剪掉一场戏是因为它是一个次要的故事情节,而且可能会让观众跳脱出主线。作为剪辑师,我很喜欢演员。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脑屏幕后面观察他们。而通常,他们并不认识我。刁亦男导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后,四位主演都拥抱了我。他们非常感谢我所做的工作。那真的是非常感人。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剪辑是一种充满了爱的行为。而在那一次,这种爱得到了回报。马修:他们的处境与导演和剪辑师很不同,因为他们往往在剧本筹备阶段就介入了。因此,他们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知道剧本是如何诞生的,也知道在写作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拍摄过程中不会消失——在剪辑过程中又会再次出现。制片人什么都知道。当然,他们不会每天都在剪辑室,也不会因为每天看8个小时的素材而感到疲倦。因此,当你展示初剪时,制片人的观点对导演和剪辑师都非常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反馈是有人说:「我不明白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很有用的。然后由导演和剪辑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文艺片不会有这种过程,因为导演的愿景和观点是最重要的,而商业片是为了吸引观众,所以会有更多这样的展示或测试,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反馈。对导演来说,展示他的电影,看看人们对它的看法,然后搞清楚他们想看些什么,总是有益的。马修:是的。这是一部素材不多的电影,松太加一开始和一个年轻的剪辑师一起剪辑。他给我看了一个版本,他知道还需要拍摄更多的场景,所以过程有点不同,因为我看到了初剪之后,他问我电影有哪些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我告诉他,结局不是很令人满意,还有一些其他建议。所以两个月后,他重拍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意见对他真的很有用,因为他完全重拍了结局。在他剪辑了新的场景之后,我「润色」了两个星期,只是做了结构上的小调整和节奏的变化。这次经历非常顺畅。问:你会偶尔去到拍摄现场,还是会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马修:在疫情爆发之前,我确实会时不时去片场,但大多数时候,我会待在酒店房间里埋头剪辑。我有时会在拍摄的第一天去。我第一次频繁去片场是拍摄《江湖儿女》的时候,因为这部电影的一部分是用35毫米胶片拍摄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素材送到实验室,实验室扫描后再把它寄给我。要过很多天我才能收到素材,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待在片场。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去片场,但实际上我不去反而更好,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需要观察影像的本质。我不应该知道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例如,我不需要知道拍摄是否因某种原因被推迟,或者导演和演员那天心情不好。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电影制作的信息都是噪音,它可能会扰乱我的工作,或者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客观地看待影像,影响我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疫情爆发之后,我就彻底不去现场了。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素材。我在台湾有一个团队,我和蔡晏珊一起工作。她是台湾人,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大约6年。她一直是我参与的许多电影的合作剪辑师。有时,在拍摄期间,她会做样片的粗剪,有时我来做。有时,她独立剪辑,然后我对她的版本给予反馈,或者我先开始剪辑。有时,我会独自剪辑大部分,最后,如果有需要,她会进行修正。与她合作的好处是,我们非常了解对方,因为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了超过15部电影。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会对镜头感到厌倦,你会失去观看影像和故事的新鲜感。所以比方说,她会先在一部电影上工作一个月,然后我看到它时仍然有新鲜的视角,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问题。反之亦然。在经历了漫长的剪辑过程之后,这很有帮助。我不喜欢那种「这是我的电影,我是剪辑师,其他人不能碰它」的心态。剪辑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它是非常务实的。要么对电影有好处,要么没有。我还有一个合作者,一名助理剪辑师,也在台湾,叫郑翊。由于我今年住在法国,时差恰恰变成了一项优势,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反之亦然。当然还有我的妻子王思静(她是一位制片人),她经常看我们的电影,并给我们提出意见。给她看的时候,我通常很紧张,因为她的批评可能会很尖锐。但是和她一起看总是很有帮助,因为我可以通过第三双眼睛来看待这部电影。马修:嗯,年底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是让-夏尔·休执导的一部电影。目前,我还在剪辑两部中国电影,一部是魏书钧导演的,我还和他合作过《永安镇故事集》。这部电影有点像黑帮片,我很喜欢!他已经拍了三分之二,我在等他完成。另一部是张一白导演的作品,但我还不能透露太多。在我与中国导演合作的同时,我也非常期待剪辑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电影。我不想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做中国电影的法国人」。中国是一个「疯狂」的地方,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有很多拍电影的好基础,有一个很大的电影产业,这非常重要,但我仍然渴望处理新的故事。我喜欢认识新的角色。马修:没有!事实上,我在学生时期确实执导过一些短片,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但自从我成为一名剪辑师后,我就不想再做导演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非常喜欢在不同的项目之间切换,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导演制作一部电影有时需要花两三年,甚至更长。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毅力。对我来说最高的赞誉是,我以前合作过的导演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剪辑他/她的新电影。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现,而信任是导演和剪辑师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将努力继续帮助导演实现他们的愿景。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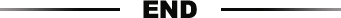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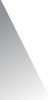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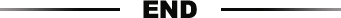

![aka小腿 没机会做你第一任女朋友 那就做你最后一任 好不好[求饶] ](https://imgs.knowsafe.com:8087/img/aideep/2021/10/6/58197bb8167b8dce79737622d206dc2d.jpg?w=250)





 虹膜
虹膜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