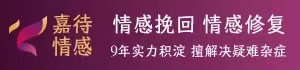德国新电影有一个人被忽视太久
作者:Daniel Eagan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Film Comment
(2023年2月13日)
 《蒙古的圣女贞德》
《蒙古的圣女贞德》打破常规对奥汀格来说很容易,她的风格结合了引人注目的服装和地点,特殊的摄影和复杂的配乐。一部90分钟电影的成本可能会衍生出一部12小时的纪录片。她的情节可能会分裂,角色可能会改变性别,流派可能会消失。
无论是纪录实验艺术「发生」的《柏林热——沃尔夫·弗斯特》(1973)中,还是探索北京、四川和云南的城市生活的《艺术——人民》(1985),亦或是描绘维也纳的游乐园的《普拉特公园》(2007),她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永不枯竭的好奇心。
 《普拉特公园》
《普拉特公园》
今年的波兰CAMERIMAGE电影摄影艺术国际影展授予奥汀格先锋电影成就奖;作为荣誉的一部分,奥汀格被邀请展示她的一些著名作品。1979年的《一个女酒鬼的肖像》放映后,我与这位电影人进行了交谈。这是一部滑头的荒诞主义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柏林闲逛,喝得酩酊大醉的故事。奥汀格选择放映另外三部代表她对纪录片、亚洲艺术和拼贴兴趣的影片:《普拉特公园》《雪之下》(2011)和《巴黎画诗》(2019)。
记者:这次电影节之行怎么样?
导演:这是我第一次来托伦。让我着迷的是,在波兰的电影节上,不仅仅有电影人。这里还有我非常欣赏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不同领域的有趣的人。
记者:你没有遵循其他艺术家所遵循的叙事规则。
导演:是的,从来没有。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只是我找到了一种适合我的方式。这从来不是挑衅——我只是想用某种方式做事。
关于如何工作,我想了很多。有时我准备得很充分,但有时我有一个无法拒绝的自发想法。你必须与周围环境互动。例如,我拍了一部关于蒙古游牧民族的纪录片[《蒙古生活》(1992)],在其中我拍摄了风景,人,以及他们在做什么。每一个镜头本身都像是一个小故事。
 《蒙古生活》
《蒙古生活》
另一方面,为了我的最新电影《巴黎画诗》,我通过观看五六百部电影进行了研究。我去调研了剧院档案、报纸档案和私人档案。我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末在巴黎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很重要的所有事情。我们拍摄了新素材,但电影本身主要是拼贴。所以我认为每个项目都必须找到合适的形式。前卫永远发生在你认为她不该出现的地方。
记者:什么样的灵感会让你开始拍一部电影?
导演:首先,我认为能看到很多东西是很好的。有时你从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始:你在街上的观察,你听到的对话。任何事情都可以是起点。
我认为你永远不应该做别人期望你做的事。重要的是,你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方式。如果结果不好,那不是灾难,这只是一个开始。
 《巴黎画诗》
《巴黎画诗》
记者:你曾经说过,地点是主人公。
导演:当我在巴黎生活后,1973年来到柏林时,我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一片灰暗,一点也不迷人。但这非常有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整个德国的历史。当你在拍摄电影时,这正是你所寻找的:可见的秘密。你不仅要看,还要理解。
记者:你都是像拍《最南航》(2002)和《蒙古生活》那样拍纪录片的么?
导演:你不能以审问者的身份去问拍摄对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我去蒙古时,我向人们展示了大量的圣经研究。照片,图纸,影印本,明信片,各种视觉材料。他们能识别物体并对其进行评论。我们一起喝茶,一起玩乐,一起唱歌,一起欢笑。这就创造了一个你可以拍摄的氛围。
我在20到25个不同国家的市场里拍摄过。它们永远是人口和文化集中的地方。例如,当我在敖德萨的鱼市为《最南航》拍摄时,那里都是女性,非常坚强的女性,她们可以回馈社会。你不能躲在柱子后面拍摄;你必须对她们说:「看起来太棒了。」这就开始了一场对话,一场互动。那么她们就不是「客体」或「主体」了。相反,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有趣的技巧。
 《最南航》
《最南航》
记者:所以你也没有什么计划?
导演:我当然有想法,但它们可能会完全改变。如果你事先知道了一切,那拍纪录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记者:你怎么确定自己解读文化的方式就是对的呢?
导演:总会有错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会说,「我不是日本专家,」但他在那里旅行时所看到的,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的人仍然无法理解。重要的不仅是你知道什么,还有你如何看待事物。
记者:你很多电影都是在亚洲取的景。
导演:我一直觉得亚洲的程式化形式很有趣。我研究过不同的亚洲戏剧。他们不受我们宗教的影响,比如基督教。他们有另一种转变的方法。对他们来说,艺术应该表现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本身就在你面前。
我给你们举个水墨画的例子。当你用水蘸墨作画时,这是一个你能看到和理解的自然过程。但与此同时,墨水和水的性质也变得不同了。它们不再是两个元素,而是第三个元素。它们结合并转化为艺术。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总是想在我的电影中达到这一点,元素转化为另一种东西。
 《蒙古生活》
《蒙古生活》
记者:我很想看你把这种想法推销给投资人。
导演:当你为一部纪录片申请资金时,他们想要一个100到150页的剧本。你能想象吗?
阿涅斯·瓦尔达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她去Canal+与资助委员会见面的故事。秋天到了,在路上她发现了一片漂亮的叶子,红黄相间。她把它放在Canal+的人面前,说:「我想拍一部关于这个的电影。」
我很想那样做,但这样来表现的话,我永远也拿不到钱。所以,你必须假装什么都知道。
拍《沙米索的阴影》(2016)时,我收到了德国一家为电影和电视设立的媒体合作基金的一些资助。他们同意买下它,并在两年后在电视上播出。我得到一笔90分钟的电影拨款,然后去白令海拍摄。当我回来剪辑的时候,他们在大约三个月后打来电话,问我:「我们能去看看吗?」我说:「不,还没到时候。」五个月后,我打电话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来了,电影快拍完了。他们说:「太好了,我们明天早上看完另一场放映后再来。」我说:「不行,你得来两天。」(《沙米索的阴影》片长有12小时。)
你能想象把这些告诉他们吗?这很危险。他们本可以把钱拿走。我们为此吵了好几个月。
记者:那最后怎么解决的?
导演:他们最终在电视上播放了电影的第一部分,我得到了更多的钱。但你必须战斗。这真的很冒险。
我收到了一些特别的报价。1985年我在四川拍了一部纪录片(《艺术-人民》)。有一个场景,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在周围打转,背景中你可以听到持续的汽车喇叭声。大众汽车公司的人找到我说:「如果我们的一辆车出现在这些自行车中间,那不是很棒吗?」我想那是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建第一家工厂。
也许我应该这么做。他们有那么多钱,我本可以再来一次中国,但我已经在去别的地方的路上了。
在《一个女酒鬼的肖像》中,有一个场景是塔贝亚·布卢门谢因穿着一件黑色晚礼服离开酒店,她比了个手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接到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他们想用它做广告。
 《一个女酒鬼的肖像》
《一个女酒鬼的肖像》
记者:你在《一个女酒鬼的肖像》中是怎么与塔贝亚·布卢门谢因合作的?她既是主演,又是服装设计师。
导演:她在那部电影里穿的是高跟鞋。她穿着鞋走路的声音成了一种主旋律——还有打碎玻璃的声音。
塔贝亚并不是真正的演员。她当时说方言——她不会说高地德语(标准德语)——所以我想,如果她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一个她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城市,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你得为塔贝亚安排好一切,但这样做奏效了。那时,她是我的伴侣,我们一起住在一个很棒的大公寓里。当时柏林的情况很奇怪:商店里摆满了奢侈品,但没有顾客。你可以买布料、羽毛、珍珠来做帽子或衣服。我们把它们都安排在一张大桌子上,然后塔贝亚开始工作。她太棒了——她能做出完美的剪裁。
她两年半前突然去世了。那是一次美妙的合作,充满了想法和幻想。
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虹膜
虹膜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