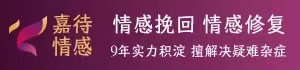公路电影和女性电影里面,这部电影都是老祖宗
作者:Manohla Dargis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
(1991年7月)
——塞尔玛《末路狂花》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40年代末为背景,但直到1957年才出版,是「垮掉的一代」对美国充满乐趣的公路生活的开创性庆祝。快车、威士忌、女人、仅剩的几块脏兮兮的钱——是嬉皮士之旅的基本要素。然后,汽车改变了美国的景观,激增的人口驾驶着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汽车急速奔驰,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继续以其「灵活报废」(Dynamic Obsolescence)计划挤占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
 《在路上》
《在路上》
在凯鲁亚克去世多年后,公路仍然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语汇,无论是罗伯特·弗兰克这样的老将,还是大卫·林奇这样的中坚力量,或是吉姆·贾木许这样的侦察员。即使美国的公路网络现在已经沦为高速公路和混凝土的无尽交缠——更接近J·G·巴拉德的世界末日式崩溃,而不是凯鲁亚克的文学式兜风——这种神话仍然存在。
当然,它也为雷德利·斯科特的新片《末路狂花》提供了动力,该片讲述了两个女性朋友因杀死强奸犯而逃亡的故事。但与它无数的同类作品不同的是,《末路狂花》不仅仅是重写了这一语汇,它还重塑了公路电影,并且是为女性量身打造的。
 《末路狂花》
《末路狂花》
公路定义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它是一片空旷的区域,是一片虚静,也是最后真正的边疆。它的神话回荡在美国电影史上,从尼古拉斯·雷的《夜逃鸳鸯》(1948)到罗伯特·奥特曼近30年后翻拍的《没有明天的人》。
公路旅行往往是男性化的,而公路电影使俄狄浦斯式的叙事对男性英雄的要求变成了某种成人仪式。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一同驱车上路,那么这段充满情欲的旅程就会滋生危险和暴力,而不是欢愉。
正如《夜逃鸳鸯》所呈现的那样,母亲的身份使蛇蝎美人的形象变得温和,但如果脱离了家庭范畴,像《雌雄大盗》或《穷山恶水》中那样,女性似乎会引发充满暴力的仪式。对于独自旅行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风险有一些变化。她们要么最终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如《惊魂记》——最终的毁灭之旅;要么落入一种边缘的亚类型,如女子监狱电影《桀骜青年》(Untamed Youth)或摩托车电影《摩托魔女》。
 《夜逃鸳鸯》
《夜逃鸳鸯》
《末路狂花》偏离了主流,聚焦于两个女人一起踏上旅途的故事。但是,将这部电影与一般的劣作明确区分开来的——使其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主角性别的偶然案例——是它通往自我的道路所采用的独特手段。
简而言之,塞尔玛和露易丝在掌握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亡命之徒。她们的罪行是自卫,她们的逃犯身份是由性别上的不自由所强加的,她们的旅程以身体的政治为基础。在女性身体以反常的方式被交易和流通的文化中,一个女人夺取对自己身体的权力仍然是一种激进的行为。
这与其他三部公路电影——约瑟夫·刘易斯的《枪疯》(1949)、乔纳森·戴米的《散弹露露》(1986)和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1990)中的性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刘易斯的漂泊爱情故事中,反英雄式男主角巴特·塔雷由于对枪支和情人安妮·劳里·斯塔尔的双重迷恋,走上了一条暴力的性狂欢之路。在这部黑色电影中,男人走向成熟的旅程以青年时期的田园环境为开始和结束,但却因为无情的女人偏离了方向。
 《枪疯》
《枪疯》
作为残酷且毫无母性形象的角色,安妮蓄意利用欲望将这对夫妇推向疯狂的犯罪行为,迫使他们走上了不归路。就像更早的《邮差总按两次铃》(一部里程数很低的公路电影)那样,女人的身体和道路是可以互换的,两者都是每个男人都必须经过的地方——仿佛违背自己的意愿一般——并最终由此走向毁灭。
情欲越轨
在乔纳森·戴米的《散弹露露》中,一个白人嬉皮士的跨国旅行有着存在主义式英雄叙事的意味,是对自我的寻找,其关键在于他对一个「野性」的、时常穿着非洲风情服装的白人女性的驯服。
在这对亡命鸳鸯的旅程中,戴米的女主人公从露露「变成」了奥黛丽,其标志为她用金发和纯白的裙子取代了红色唇膏、黑色假发和非洲服饰。这一转变似乎是为了缓解令人不安的目的论,戴米同时将其与一群「形象积极」的黑人配角并置——宅男、去教堂的人、一个唱歌的牛仔。
 《散弹露露》
《散弹露露》
如果说戴米的故事包含了一种善意的自由主义,那么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则是其反面的附属品。作为一部后现代版《绿野仙踪》的公路电影,《我心狂野》充斥着林奇惯常的执念——异常(身体和其他方面)、虐待狂式的残酷行为、性犯罪。卢拉·弗琼和塞勒·雷普利是一对逃亡中的年轻恋人,他们的「黄砖路」上充斥着自由和情欲越轨,试图逃脱卢拉的疯子母亲的控制,这个女人被想象成东方恶巫的化身。
在影片开始之前,卢拉的身体就已经被征服了(她在青少年时期遭遇强奸)。这是一个有待探索、蹂躏并最终被驯化的领域——经由母亲身份与婚姻的加持。
和《散弹露露》一样,《我心狂野》中的女性身体是有争议的领域,只不过这里的冲突更隐蔽。在影片中,围绕卢拉和旅程的斗争是由一个黑人男子的死亡引发的,后者在影片一开场就被塞勒爆头了。后来,在另一个怪诞的场景中,一个白人妇女对另一个黑人男子大喊「操我」,而该黑人男子对夹在他们中间的白人男子扣动了扳机。
 《我心狂野》
《我心狂野》
对种族混合的恐惧困扰着这部电影,频频有人死亡。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这片土地也是我的土地——但不要碰那些白人妇女。财产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而塞勒对于财产特权的认知就像他的蛇皮夹克一样华丽繁复,正如他提醒卢拉的那样,那是「我的个性和个人自由信念的象征」。
仿佛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直接回应,《末路狂花》中的一个关键场景是一位黑人拉斯塔法里教徒骑车进入画面,十分不协调。塞尔玛和露易丝抢了一个公路巡警的枪——象征性的阉割——并把他锁在汽车后备箱里。在女人们离开后,从暴徒沦落为软蛋的男人扭动着一根白色的瘦小手指,而那个拉斯塔法里教徒则吐出了一口烟作为回应。美国的风景已经不再是白人男子气概的专属领域。

虽然《末路狂花》并没有假装要纠正压迫的传统,但它确实作为一部女权主义公路电影而存在。更加有趣的是,它也是一部西部片,只不过用的是点45手枪而不是温切斯特步枪,开的是66年的福特T-Bird车而不是70年代推出的福特平托车。
塞尔玛和露易丝身上有着经典的西部角色的影子,但又有所变化。塞尔玛单纯而可爱,像孩子一样,不谙世事——她是约翰·韦恩在《红河》的序幕中吻别的女人,是《大江东去》中的玛丽莲·梦露,以及《乱点鸳鸯谱》中更为悲伤版本的梦露。露易丝坚韧而有见地,是一个酒馆女郎——就像《碧血烟花》中的玛琳·黛德丽或《西部人》中的朱莉·伦敦。「这个周末不行,亲爱的」,露易丝跟一个男同事谈及塞尔玛时开玩笑说,「她要和我私奔」。影片一开始似乎是女性对男性气质的退避,一场周末的睡衣派对,最后变成了一场关于女性友谊、枪支和胆量的冒险。

跨越边界
塞尔玛和露易丝在离开小镇时或许是满面笑容的,穿着多莉·帕顿式的牛仔服和蕾丝,但她们的逃离之旅一离开家园就变得丑陋不堪。在她们的第一站,塞尔玛在停车场被一个与她跳舞和调情的男人袭击了。
而影片在露易丝打断强奸的那一刻宣布了它的意图,她用一颗子弹穿过男人的胸膛作为对「给我口交」的霸道指令的回答。与《我心狂野》不同,这一领域并没有开放给人利用。当这些女人再次上路时,她们不是在躲避男人,而是在逃避法律——不仅仅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或约翰·埃德加·胡佛,更是父权的法律。
与邦妮和克莱德相比,塞尔玛和露易丝的罪行不是谋杀,而是其主体。在《末路狂花》中,处于危险之中的是父权——无论是名为哈伦的强奸犯、塞尔玛令人讨厌的丈夫,还是父亲般的哈尔。在《大地惊雷》和《沉默的羔羊》中,强大的女性角色依靠男性,或从男性那里学习进步。在《末路狂花》中,女性为了生存而相互依靠。

在通常的性别语境中,女性的欲望等同于被动,男性的欲望等同于主动,这是《末路狂花》颠覆的一种老生常谈。正是这种熟悉的逻辑将众所周知的先锋女性囿于一个小木屋之内,并将《漂亮女人》中的好莱坞妓女式角色推搡到公寓的安全出口处当成某种爱情战利品。在相似的叙事套路中,塞尔玛是一个晕头转向的家庭主妇,嫁给了一个蛮横的地毯推销员。「他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父亲」,露易丝如此提醒她的朋友。在路上,塞尔玛在电话中向她的丈夫重复了这句话,宣告了她的独立和重生。
与那些让女性接受虚假的性别转换的电影不同(如布莱克·爱德华兹的《变男变女变变变》),《末路狂花》中的转换不仅仅是表面的。就像在《散弹露露》中,服装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卢拉剥离了「异国情调」以回归本质,用危险换取绅士风度,用黑色替代白色,《末路狂花》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模式。

露易丝取下了她所有的首饰——包括订婚戒指——转而戴着一顶白色的牛仔帽,塞尔玛则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上面印有一个微笑的骷髅头和《夺走我的生命》(Drivin’ my life away)的歌名。但是,这两个亡命之徒的装扮并不只是男性化那么简单,当露易丝把她的口红扔到泥土里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一个突发的奇思妙想。
身体上的转变与两人在美国公路上的狂奔并行不悖。她们每越过一个州的边界——就意味着存在主义层面和字面意义上的边界被一同跨越。在《末路狂花》中,凶杀和混乱与女性友谊的意义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就像《散弹露露》的美国公路之上充斥着白人的俗气和黑人的文化一样,《末路狂花》也呈现了相应的男性气质。露易丝无视了旁边那个正在加油的、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肌肉男,对加油站的服务员说:「加满油。」牛仔、亡命之徒、警官:斯科特的画面中一一出现了这些彰显着男子气概的角色。塞尔玛的粗鲁丈夫达里尔;两个女人的牛仔情人J.D.和吉米;友好的阿肯色州警察局长哈尔,以及不公正的法律似乎变成了例外——传统的主角在这里被沦为了配角。
男人的缺席
吉米是一位巡回演出的音乐家,他是新时代的牛仔,有着歌星克里斯·艾萨克般的魅力,而J.D.戴着宽边牛仔帽,臀部丰满,是《巨人传》和《穷山恶水》中的那种芳心纵火犯——影片中唯一越过人体的镜头是塞尔玛对他块块分明的腹肌的凝视。男人是这段捉摸不定的女性之旅的路标——好的、坏的和丑的,每一个男人都暗示着不同的异性恋可能性,以及潜在的庇护或威胁。
从《逍遥骑士》到《虎豹小霸王》再到《午夜狂奔》,「哥们电影」(buddy movie)中的男人们为了巩固他们的个人自主权而建立了一种关系。
相比之下,《末路狂花》建立的纽带并不是基于共同的自恋情结和私人特权——或对男人的争宠。这在一个场景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两位女主角在夜色中奔驰,背景是红色的山丘和壮阔的景观。这场戏气势恢宏,是经典的边疆场景,极易引人联想到约翰·福特最令人难忘的西部片。

而在《末路狂花》的开场画面中,当充满怀旧气息的黑白画面让位于鲜艳的色彩时,似乎是对胶片本身特质的致敬。这幅全景图一目了然地唤起了妇女既被驯化又未开化的地方——就像《关山飞渡》中的母亲和妓女——而土地,就像两位女主角一样,既是好的又是坏的,既是丰饶的又是折磨的,既是野性的又是驯服的。
就在这些山峰之间,塞尔玛和露易丝迎来了影片中最亲密的时刻。当玛丽安娜·菲斯福尔沧桑的嗓音唱响《露西·乔丹的歌谣》时,塞尔玛和露易丝交替喝了一口野火鸡威士忌:「在37岁的时候,她意识到她永远不会开着跑车穿过巴黎,任由暖风拂过她的头发。」后来,两人把车停在路边,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黎明的到来,火橙色的太阳、赭红色的山丘和她们猩红色的头发交映生辉,令人心惊。

在较为笨拙的导演手中,这一刻可能会陷入模糊的本质主义。但在《末路狂花》中,问题不是女人的本性,而是展露本性的女人。在这里,女性的身体并不是有待描绘的风景,或需要征服的领域。这是被解放的身体,但同时也是具有共鸣性的身体。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塞尔玛和露易丝在路上创造了一种女性友谊的典范——萌发于她们对男性世界及其法律规范的任性拒绝。无论她们的旅程最终在哪里结束,塞尔玛和露易丝都在美国银幕上重新塑造了姐妹情谊。
重访公路
杰克·凯鲁亚克长年酗酒,在写完他最著名的书近20年后隐居而死。《在路上》中令人眩目的男性气质的承诺也就到此为止。66号公路已被废除,底特律几乎死气沉沉。如今,美国政府为满足其汽车需要的石油而发动战争。

在《末路狂花》中,美国公路电影的历史通过修正主义式的镜头进行了过滤。一步一步地,塞尔玛和露易丝仿佛重走了熟悉的路线,但带着愉悦而非权力性的意志。乏味的场景和老套的风景都被重塑,以新的视角和从未被讲述过的生活而迎来复苏。在这次旅行中,当女人掌握方向盘时,男人就被远远甩在了身后。
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虹膜
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