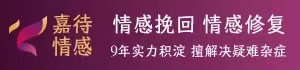作者:杰里米·O·哈里斯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Interview
(2023年10月12日)
滨口龙介电影的核心诗意往往来自于俗日:错过的际遇、砍伐的木头、与同事的畅饮。在他的最新影片《邪恶不存在》中,这种诗意与一种政治意味并置在一起,让人不禁脊背发凉,并意识到资本主义不仅在迅速侵蚀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在侵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邪恶不存在》在标准收藏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安静办公室里,滨口和我在他的翻译员莫妮卡的帮助下谈论了他的作品。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们谈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剧作家、语言的局限性、电影如何填补空白,以及这位日本最令人兴奋的新兴电影人是否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何时会拍摄他的第一部英语长片。
《邪恶不存在》在标准收藏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安静办公室里,滨口和我在他的翻译员莫妮卡的帮助下谈论了他的作品。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们谈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剧作家、语言的局限性、电影如何填补空白,以及这位日本最令人兴奋的新兴电影人是否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何时会拍摄他的第一部英语长片。 杰里米·O·哈里斯、滨口龙介、莫妮卡哈里斯:你仍然能给人惊喜。事实上,你拍剧情长片不过才十年,你的第一部电影就备受赞誉。你还是第三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的日本导演,而且本土电影界对你的评价也颇高。你对此有何感想?最初刚开始拍摄纪录片和剧情片时,你是否预料到会有现在的成就?滨口龙介:首先,我要再次感谢你对我的电影生涯如数家珍。当然,我不能说这些都是我预料之中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只想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大家的热烈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另一方面,我确实觉得我的职业生涯有了某种进步,我非常感激并接受对我个人作品的任何形式的支持。
杰里米·O·哈里斯、滨口龙介、莫妮卡哈里斯:你仍然能给人惊喜。事实上,你拍剧情长片不过才十年,你的第一部电影就备受赞誉。你还是第三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的日本导演,而且本土电影界对你的评价也颇高。你对此有何感想?最初刚开始拍摄纪录片和剧情片时,你是否预料到会有现在的成就?滨口龙介:首先,我要再次感谢你对我的电影生涯如数家珍。当然,我不能说这些都是我预料之中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只想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大家的热烈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另一方面,我确实觉得我的职业生涯有了某种进步,我非常感激并接受对我个人作品的任何形式的支持。 滨口龙介哈里斯:当一位像你这样的国际级导演开始被西方或美国电影界追捧时,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人们会开始频频询问你什么时候拍摄一部英语电影。你有这个打算吗?滨口龙介:的确,我收到过不少提案,也对其中一些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用非母语的语言工作的。我担心的一点是,使用非母语来指导别人,可能会出现理解偏差。所以,如果要让我去拍一部外语片,我认为需要循序渐进,也许其中仍然会包含日语的部分。哈里斯:就我个人的角度而言,看着一部为美国黑人主角创作的戏剧在日本由完全本土化的日本演员演绎,我会觉得非常新奇,我认为必要的基于身份的意义塑造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不少磨合。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往往发生在英语电影中的事情,在日本演员的演绎下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让我感觉就像在看我本人的故事,但又好像是在看网飞制作的作品,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而已。片中扮演母亲的那个女演员表现得非常出色。如果演员演得好,我想他们就能传达出创作者的意图。
滨口龙介哈里斯:当一位像你这样的国际级导演开始被西方或美国电影界追捧时,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人们会开始频频询问你什么时候拍摄一部英语电影。你有这个打算吗?滨口龙介:的确,我收到过不少提案,也对其中一些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用非母语的语言工作的。我担心的一点是,使用非母语来指导别人,可能会出现理解偏差。所以,如果要让我去拍一部外语片,我认为需要循序渐进,也许其中仍然会包含日语的部分。哈里斯:就我个人的角度而言,看着一部为美国黑人主角创作的戏剧在日本由完全本土化的日本演员演绎,我会觉得非常新奇,我认为必要的基于身份的意义塑造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不少磨合。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往往发生在英语电影中的事情,在日本演员的演绎下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让我感觉就像在看我本人的故事,但又好像是在看网飞制作的作品,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而已。片中扮演母亲的那个女演员表现得非常出色。如果演员演得好,我想他们就能传达出创作者的意图。 《驾驶我的车》哈里斯:是的,你似乎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我很喜欢《夜以继日》和《驾驶我的车》,还有《邪恶不存在》。这些作品中的很多角色都对契诃夫情有独钟。这是从何而来的?你一直都是戏剧的创作者和观众吗?
《驾驶我的车》哈里斯:是的,你似乎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我很喜欢《夜以继日》和《驾驶我的车》,还有《邪恶不存在》。这些作品中的很多角色都对契诃夫情有独钟。这是从何而来的?你一直都是戏剧的创作者和观众吗? 《驾驶我的车》滨口龙介:其实我算不上对戏剧特别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融入戏剧元素的电影。比如雅克·里维特或约翰·卡萨维蒂的作品,甚至是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关于剧院的纪录片。在这些类型的电影中,我真正喜欢和感到舒服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你会看到表演是一种隐藏的、不显眼的姿态,但在戏剧中,表演似乎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戏剧演员在演戏,而且他们并没有假装自己没有在演戏。这就是我开始对契诃夫感兴趣的原因。事实上,我经常被问到关于契诃夫的问题。我确实看过一些戏剧,我也在日本看过契诃夫戏剧的演出,但老实说,我并未觉得它们特别有趣。后来,我读了他的剧本,仿佛每个字都给了我一拳,它们完全引起了我的共鸣。此外,在《夜以继日》中,我借鉴了契诃夫戏剧中的一句台词,我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我只是自然地把它融入了影片之中,因为它让我深深共鸣。
《驾驶我的车》滨口龙介:其实我算不上对戏剧特别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融入戏剧元素的电影。比如雅克·里维特或约翰·卡萨维蒂的作品,甚至是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关于剧院的纪录片。在这些类型的电影中,我真正喜欢和感到舒服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你会看到表演是一种隐藏的、不显眼的姿态,但在戏剧中,表演似乎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戏剧演员在演戏,而且他们并没有假装自己没有在演戏。这就是我开始对契诃夫感兴趣的原因。事实上,我经常被问到关于契诃夫的问题。我确实看过一些戏剧,我也在日本看过契诃夫戏剧的演出,但老实说,我并未觉得它们特别有趣。后来,我读了他的剧本,仿佛每个字都给了我一拳,它们完全引起了我的共鸣。此外,在《夜以继日》中,我借鉴了契诃夫戏剧中的一句台词,我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我只是自然地把它融入了影片之中,因为它让我深深共鸣。 《夜以继日》哈里斯: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确实都在试图找出人类如何彼此坦诚,以及他们如何对自己坦诚。我觉得你和他们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我很好奇,你在自己的作品中想要了解的是些什么?滨口龙介:这其实很复杂,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读过契诃夫的作品,其中每个字对我都很有冲击力,我确实也感受到了每个人物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内心从文字中流露出来。此外,我意识到的一点是,这些文字几乎是一连串的独白,每个角色都没有真正地去考虑其他人,而易卜生等人则更注重对话。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似乎就是一系列独白,这也是我所思考的,并试图将其融入《驾驶我的车》这样的电影中。再回到我对戏剧的兴趣上,我认为有一种情感只有通过表演才能达到。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欺骗,但在戏剧的框架内,观众非常自愿地参与其中,并且非常支持这种环境的营造,进而主动接受这种表演。因此,当你思考情节剧,想到情节剧的虚构性和虚假性时,你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戏剧,以及观众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其中,愿意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夜以继日》哈里斯: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确实都在试图找出人类如何彼此坦诚,以及他们如何对自己坦诚。我觉得你和他们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我很好奇,你在自己的作品中想要了解的是些什么?滨口龙介:这其实很复杂,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读过契诃夫的作品,其中每个字对我都很有冲击力,我确实也感受到了每个人物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内心从文字中流露出来。此外,我意识到的一点是,这些文字几乎是一连串的独白,每个角色都没有真正地去考虑其他人,而易卜生等人则更注重对话。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似乎就是一系列独白,这也是我所思考的,并试图将其融入《驾驶我的车》这样的电影中。再回到我对戏剧的兴趣上,我认为有一种情感只有通过表演才能达到。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欺骗,但在戏剧的框架内,观众非常自愿地参与其中,并且非常支持这种环境的营造,进而主动接受这种表演。因此,当你思考情节剧,想到情节剧的虚构性和虚假性时,你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戏剧,以及观众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其中,愿意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驾驶我的车》哈里斯:我都快哭了,因为我觉得你的艺术模式与我非常一致,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题外话,你真是一位很棒的翻译员。哈里斯:我知道翻译员往往应该隐居幕后,但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因为你真的非常棒。滨口,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话语或作品不断经过翻译的过滤?滨口龙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成为导演之前,我是一个影迷,而观看和欣赏非母语电影的一大难关就在于阅读字幕。我常常被字幕所打动。我认为我对翻译和字幕本身的总体看法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懂一些英语,我会在看电影的时候阅读英文字幕,我明白没有直接而完美的翻译,也没有办法把日语的真正含义完全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驾驶我的车》哈里斯:我都快哭了,因为我觉得你的艺术模式与我非常一致,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题外话,你真是一位很棒的翻译员。哈里斯:我知道翻译员往往应该隐居幕后,但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因为你真的非常棒。滨口,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话语或作品不断经过翻译的过滤?滨口龙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成为导演之前,我是一个影迷,而观看和欣赏非母语电影的一大难关就在于阅读字幕。我常常被字幕所打动。我认为我对翻译和字幕本身的总体看法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懂一些英语,我会在看电影的时候阅读英文字幕,我明白没有直接而完美的翻译,也没有办法把日语的真正含义完全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邪恶不存在》因此,当你观看画面时,注意到的可能是演员的肢体动作,甚至是演员静止不动时的细微动作。这些都会被接收到。声音总是直接被观众接收,文字则不尽然。因此,如果你读字幕时领会了其中80%至90%的意思,剩下的就可以通过声音和画面来补全。我认为,正因为字幕和翻译可以作为这种理解的桥梁,所以我对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村上春树说过,必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翻译一部作品,相信自己能在原作和译作之间建立起亲密的桥梁,相信自己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合适人选。我认为这种信念与表演非常相似。我写了一个剧本之后,需要由演员演绎出虚构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与演员本人大相径庭,但演员需要有信心和信念,相信自己是演这个角色的合适人选。写在剧本上的内容和演员的表演之间会存在一些微小的变化或转变,这与翻译非常相似。
《邪恶不存在》因此,当你观看画面时,注意到的可能是演员的肢体动作,甚至是演员静止不动时的细微动作。这些都会被接收到。声音总是直接被观众接收,文字则不尽然。因此,如果你读字幕时领会了其中80%至90%的意思,剩下的就可以通过声音和画面来补全。我认为,正因为字幕和翻译可以作为这种理解的桥梁,所以我对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村上春树说过,必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翻译一部作品,相信自己能在原作和译作之间建立起亲密的桥梁,相信自己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合适人选。我认为这种信念与表演非常相似。我写了一个剧本之后,需要由演员演绎出虚构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与演员本人大相径庭,但演员需要有信心和信念,相信自己是演这个角色的合适人选。写在剧本上的内容和演员的表演之间会存在一些微小的变化或转变,这与翻译非常相似。 《邪恶不存在》哈里斯:很高兴你提到了易卜生,因为我在看《邪恶不存在》的时候,就心想:「这是他的易卜生时刻,这是对《人民公敌》的改编。」你当时有参考这部作品吗?滨口龙介:很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之前并没有看过这部戏剧。之前在威尼斯参加放映活动时,我被问了一遍又一遍:「你读过《人民公敌》吗?」我都回答:「没有。」在过去的70年里,没有任何新的日语译本,这算是我的借口,但后来我一读到它就发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仔细想想,我作为编剧的感知更接近易卜生,而不是契诃夫。我并不是想把每个人物的特点或视角孤立出来。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现真实的人性。滨口龙介:是的,我很喜欢这部戏剧。我认为易卜生的很多作品都把真相作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东西,真相的确具有摧毁社会的力量。哈里斯:没错。我还想问问关于音乐的问题。你是怎么考虑配乐的?你在拍一些长镜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噢,一旦加上配乐,这就会变成某种交响乐作品了?」滨口龙介:可以说,音乐与画面的搭配往往需要非常契合。有些东西是我事先想好的。例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我知道它需要出现在开头,也知道它需要出现在结尾。但因为这是一部融入了大量音乐并围绕音乐展开的电影,所以我只是尝试着将不同的配乐元素与场景相结合,然后再看看哪些元素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石桥英子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她的很多歌曲都跟影片十分契合。在剪辑影片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瞬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部分。我认为这让我可以在影片中使用大量的音乐,但又不会过火,而且音乐和影像的结合非常恰当。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改编或排演过易卜生或契诃夫的作品?
《邪恶不存在》哈里斯:很高兴你提到了易卜生,因为我在看《邪恶不存在》的时候,就心想:「这是他的易卜生时刻,这是对《人民公敌》的改编。」你当时有参考这部作品吗?滨口龙介:很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之前并没有看过这部戏剧。之前在威尼斯参加放映活动时,我被问了一遍又一遍:「你读过《人民公敌》吗?」我都回答:「没有。」在过去的70年里,没有任何新的日语译本,这算是我的借口,但后来我一读到它就发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仔细想想,我作为编剧的感知更接近易卜生,而不是契诃夫。我并不是想把每个人物的特点或视角孤立出来。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现真实的人性。滨口龙介:是的,我很喜欢这部戏剧。我认为易卜生的很多作品都把真相作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东西,真相的确具有摧毁社会的力量。哈里斯:没错。我还想问问关于音乐的问题。你是怎么考虑配乐的?你在拍一些长镜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噢,一旦加上配乐,这就会变成某种交响乐作品了?」滨口龙介:可以说,音乐与画面的搭配往往需要非常契合。有些东西是我事先想好的。例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我知道它需要出现在开头,也知道它需要出现在结尾。但因为这是一部融入了大量音乐并围绕音乐展开的电影,所以我只是尝试着将不同的配乐元素与场景相结合,然后再看看哪些元素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石桥英子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她的很多歌曲都跟影片十分契合。在剪辑影片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瞬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部分。我认为这让我可以在影片中使用大量的音乐,但又不会过火,而且音乐和影像的结合非常恰当。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改编或排演过易卜生或契诃夫的作品? 《邪恶不存在》哈里斯:我从未改编过契诃夫或易卜生的作品,倒是改编过布莱希特。我是个有点吵闹的人。我想进入易卜生和契诃夫作品中的那种安静,但我还没有做到。我的好朋友艾米·赫尔佐格刚刚与杰西卡·查斯坦合作改编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非常棒。还有安妮·贝克,她就像是美国的新契诃夫,她对契诃夫的改编非常棒,我很喜欢。易卜生真的很难改编,他的很多特质在当代作家身上都很难找到。
《邪恶不存在》哈里斯:我从未改编过契诃夫或易卜生的作品,倒是改编过布莱希特。我是个有点吵闹的人。我想进入易卜生和契诃夫作品中的那种安静,但我还没有做到。我的好朋友艾米·赫尔佐格刚刚与杰西卡·查斯坦合作改编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非常棒。还有安妮·贝克,她就像是美国的新契诃夫,她对契诃夫的改编非常棒,我很喜欢。易卜生真的很难改编,他的很多特质在当代作家身上都很难找到。 《玩偶之家》滨口龙介:你所说的关于契诃夫和易卜生的东西很有意思,尤其是关于契诃夫,他们的作品如果经过恰当的改编会非常有趣。我想这也是我对在日本看到的戏剧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哈里斯: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拍不好契诃夫的作品。滨口龙介:能够以保留趣味性的方式诠释契诃夫的导演少之又少,尽管我看到过一些有趣的尝试。至于易卜生,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每次我看或读易卜生的戏剧,我都会想:「多么恐怖的故事啊。」但在恐怖中又蕴含着某种真实,我认为这种作品在今天真的很难翻拍。这也是我想挑战自己去做的事情。哈里斯:采访时间快到了,我还想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你看过《熊家餐馆》或《正常人》吗?哈里斯:保罗·麦斯卡和阿尤·艾德维利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两位演员。我想如果你考虑翻拍一部哈内克风格的自己的作品,我会很感兴趣由他们来重演《夜以继日》。
《玩偶之家》滨口龙介:你所说的关于契诃夫和易卜生的东西很有意思,尤其是关于契诃夫,他们的作品如果经过恰当的改编会非常有趣。我想这也是我对在日本看到的戏剧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哈里斯: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拍不好契诃夫的作品。滨口龙介:能够以保留趣味性的方式诠释契诃夫的导演少之又少,尽管我看到过一些有趣的尝试。至于易卜生,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每次我看或读易卜生的戏剧,我都会想:「多么恐怖的故事啊。」但在恐怖中又蕴含着某种真实,我认为这种作品在今天真的很难翻拍。这也是我想挑战自己去做的事情。哈里斯:采访时间快到了,我还想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你看过《熊家餐馆》或《正常人》吗?哈里斯:保罗·麦斯卡和阿尤·艾德维利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两位演员。我想如果你考虑翻拍一部哈内克风格的自己的作品,我会很感兴趣由他们来重演《夜以继日》。 《熊家餐馆》哈里斯:完全可以。如果你愿意签合同,我现在就让他们去准备。这是我的梦想。哈里斯:这是你第二次来参加纽约电影节。你在纽约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滨口龙介:我每次来纽约都会去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的伟大之处在于,你不可能一次看到它的全貌,我觉得纽约人很幸运,可以免费参观。
《熊家餐馆》哈里斯:完全可以。如果你愿意签合同,我现在就让他们去准备。这是我的梦想。哈里斯:这是你第二次来参加纽约电影节。你在纽约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滨口龙介:我每次来纽约都会去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的伟大之处在于,你不可能一次看到它的全貌,我觉得纽约人很幸运,可以免费参观。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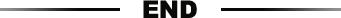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邪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 杰里米·O·哈里斯、滨口龙介、莫妮卡
杰里米·O·哈里斯、滨口龙介、莫妮卡 滨口龙介
滨口龙介 《驾驶我的车》
《驾驶我的车》 《驾驶我的车》
《驾驶我的车》 《夜以继日》
《夜以继日》 《驾驶我的车》
《驾驶我的车》 《邪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 《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 《熊家餐馆》
《熊家餐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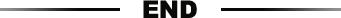







 虹膜
虹膜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