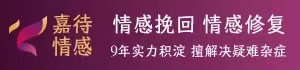啦啦小队的青年精神

“
朋克摇滚乐手贝林·米娅(Mia Berrin)讨论使用高中女生的形象来表达她作为一个奇怪的、复杂的女性的真相。

文:yzy 编:桃子
“这件服装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啦啦小队的米娅·贝林谈到她喜欢高中女生啦啦队长的风格。“我完全改变了人们看待我的方式。”
当米娅·贝林在2017年左右开始第一次作为啦啦小队(Pom Pom Squad)演出时,听众会在演出结束后接近她,并承认他们被自己的陶醉所惊讶。
“不止一次,有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本应该恨你,’”她说着,在她位于布什维克的布鲁克林的公寓里,一笑置之。“或者另一个,尤其是帅哥们,经常说‘我想着你们会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乐队。’”

相反,贝林一边演奏粗糙、邋遢的朋克摇滚,一边以高中女生的风格展示自己,她经常穿着那套自己依旧喜爱的高中女生啦啦队长的制服。当她穿上那套制服,她就意识到视觉刻板印象所带来的全部期望。
“这套服装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我完全改变了人们看待我的方式。” 她说。“在这之前,”她又补充道,“我不认为我有吸引力,也不觉得自己善于交际或很受欢迎。突然间,我又被当作食物链的顶端来对待。”
随着啦啦小队的全线首演,《啦啦队长之死(Death of a Cheerleader)》,23岁的贝林继续演绎她正在扮演的角色。她混合了她所体现的女性气质,以及所有正在愈合的青少年感情、情感负担和身份危机,用以创造一个美丽的原始朋克记录。

“专辑的标题试图扼杀我在为别人表演时的女性气质——啦啦队长是我躲在传统女性气质的斗篷里的一个形象,并非适合所有人,”她说,“但绝对适合我。”
贝林在奥兰多的童年时期尝试扮演过很多角色。那时她是一个安静的小孩,总是面带微笑,跟在更开朗的哥哥姐姐身后晃。她喜欢听歌,经常偷用妈妈的iPod,在披头士、诺拉·琼斯、娜塔莎·贝丁菲尔德的演奏中来回沉沦。她的父母直到贝林九、十岁加入当地一个青年合唱团时,才听到她唱歌。
后来的几年里,她开始想象一个未来,在那里她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任何种类的,真的。那时,演戏是她的首要任务,但她也画画写日记。私下里,她还录制自己用原声吉他唱歌的小样。慢慢地,她获得了在奥兰多的露天剧场里翻唱歌曲的信心,她把这总结为“解放天性”。

“好像有一个穿着拖鞋的白人爸爸,唱的是封面是‘变低’的专辑,”她回忆丰富,“然后还有在街上忙碌的民间朋克人。这些都成为我在观众前表演的介绍。”
贝林当时是独奏,直到她高中毕业,加入乐队的想法在她看来都还很陌生,像是“更勇敢的人,更白的白人,或是男人会做的事一样。”
在那时,贝林说,她开始变成“一个愤怒的小孩”。作为性少数者和混血(她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混血),她在一个白人占多数、基督教、异性恋的地方长大,她觉得孤独。

“我认为当你长大后,你会学到一点残忍和残忍的能力,”她说。“这是很难相信,也是很难理解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怎样应对。”
她的父母很年轻,所以贝林在高浓度的二十世纪流行文化下长大。当她进入高中后,就是她儿时看的电影和青少年节目的“自我预言实现”。但是因为要和周围的青年保持相似,她觉得有顺从的必要。
在她第一次上公立高中时,贝林受到了严重的校园暴力,最终导致她休学并在家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一点都不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她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把她安置到当地的私立高中,让她上学。这里有从她先前学校“充分拔萃”的有厚重特权外壳的八十人。作为一个有色年轻女孩,她决定适应这种“邻家女孩”的氛围,照着《十七》杂志美白,把头发染成浅棕色还有画雀斑。
尽管如此,她的同龄人还是残忍的从不让她忘记她不像她们。一个同学做了一个小测试,将贝林不太轻盈的头发和她头发的质地进行比较,并表示它们不一样。
她为相似性做的努力确实保护了她一点。“我被那群受欢迎的女孩们接纳,但是我有时脱离这个群体来看自己,”她回忆道,“有一次我们正要出发,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和她们,然后觉得我有什么东西完全不对劲。”

2016年6月在布鲁克林,拉拉小队的米娅·贝林
贝林在自己儿时卧室建立啦啦小队时还是个高中生。她已经被纽约大学录取参加表演课程,正在用音乐来平息上大学前的焦虑。她写的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是《卢克斯(Lux)》,也录入在《啦啦队长之死》里。
她自己录了一个小样然后在大学的第一周上传上去。勇敢的行为得到了回报,这首歌在布鲁克林的卫星电台里播放。
“这种我在卧室里做的东西以那种方式引起了注意,这让我感到震惊和奇怪。”她听起来仍然很惊讶。

大学有了新挑战。“文化表演非常多,‘做一个好相处的人,让自己变成一块白板。’”她说。她仍然没有为自己的身份或想要的生活而安定下来,她想要探索自我。直到她发现了《新秀杂志》、暴女文化和女权主义才找到了答案。
“(新秀)是我第一次探索以其他方式生活的青少年,”她说。“它真的指明了我在生命中能做的一切。“
她的音乐榜样——比基尼杀手(Bikini Kill)、洞(Hole)、贝特西的天堂(Heavens to Betsy)和百变顽童(Bratmobile)——帮她疏导多年来一直酝酿在心里的愤怒。她退订了《十七》然后开始探索其他的着装方式,比如她的头发为了使一位表演老师懊恼而变绿。

“看到女人尖叫、生气、混乱、开放,说着什么‘丑陋’或是争议或随便什么事……我觉得在情感上十分有代表性,”她说,“感觉突然有人帮我松开皮带。”
啦啦小队从那时起发展迅速。在贝林遇到欧菲利亚之梦(Ophelias)的斯宾塞·佩佩特(Spencer Peppet)之前,还未实现拥有自己乐队的梦想,前者的乐队是贝林私下认识的第一个全部以女性的音乐家为主角的乐队。
她和佩佩特成为了好朋友以及重要合作者,还出现在《啦啦队长之死》中的几首歌里。(欧菲莉亚之梦现在抛弃了当时使用的“全女性”的描述,因为他们有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的成员。)
贝林仍然在表演学校站稳脚跟,但她在纽约大学建立的关系似乎正推动她更多地走向音乐。在参演一个短片中“公寓派对一幕”时,贝林遇到两个提出帮她制作EP的男人。
她对男人们谎称正在写EP,于是真的冲回家做了一个,发现了自我强制的最后期限真的令人兴奋。但在录音棚,怀疑开始弥漫。她意识到自己独自工作了这么久,以至于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传达音乐品味或是意图。

“我感觉应该为自己超级无知而尴尬的事被指明了,”贝林说。这次的经历让她觉得被小瞧了,并发誓再也不要被置于那种境地了。
表演学校已经足够让人沮丧了,谢天谢地她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转到纽约大学的音乐专业,这样她就可以学着自己去做每一件事。

2016年6月在布鲁克林,拉拉小队的米娅·贝林
在啦啦小队的现场演出中,贝林开始接触自己最脆弱也是最勇敢的部分,从科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获得灵感,她学会了用“超级女性”的穿着方式来表现自己。
贝林研究并接受了啦啦队长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她说,流行文化认为这一类人经常是‘学校里最大、最吓人’的人,另一方面,她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蠢蛋’。还有第三方面,”她补充道,“我认为最近人们用健壮的运动员和复杂的人物重新诠释了啦啦队员。”
作为一个性少数者,贝林同样在欲望和吸引力的角度着迷于啦啦队员,有时,变成她们的欲望和与她们在一起的欲望会交织在一起。

贝林的性少数和帮助她理解性少数的初恋是《啦啦队长之死》的巨大灵感,她用她引以为傲的永久乐队成员阵容完成了这次录制。
她用过去的两年时间完成了这张专辑(包括她在纽约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并在关于和某个教给她“很多性少数群体以及它在我心里占据的空间的事”的人恋爱的歌曲里说了很多煽动性事件。
对于贝林来说,啦啦小队的首次亮相反映了她对自己持续不断的深入和对某些来自他人的期望的释然。在某些方面,音乐把她儿时拥有的快乐带回来了。

“这一切都会持续下去,”她说,“但是乐队对我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催着我去更多的了解自己。”
References:
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features/pom-pom-squad-death-cheerleader-interview-1189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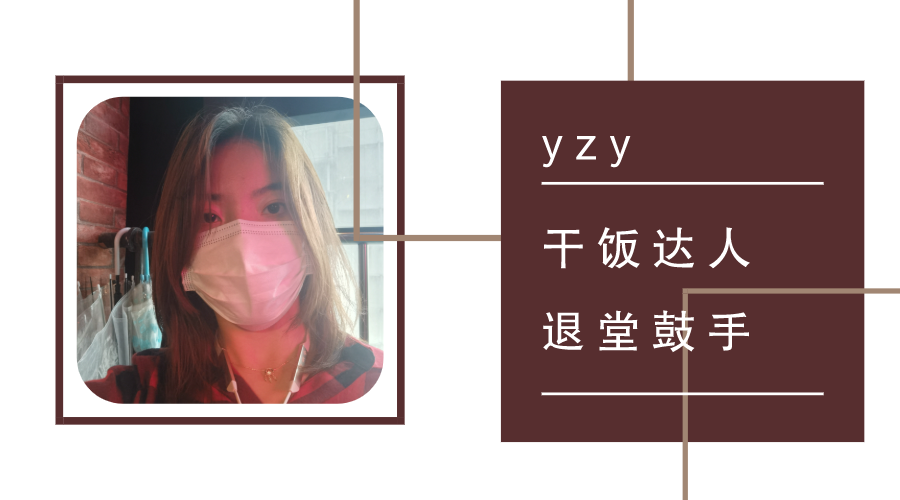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摇滚天堂
摇滚天堂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