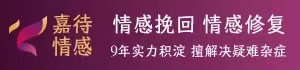澡堂阁楼上的女人们:午夜,我接到了她失踪的电话



01/知音
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最害怕午夜接到来自家里的电话,因为一般来说,只有噩耗才难以挺过漫长的夜晚。
江白露就是在那样一个麻烦缠身的午夜接到父亲电话的,父亲言简意赅:你妈找不着了,三天了。
此时此刻江白露正窝在床上赶一篇公关稿,一天前手上一个两百万粉丝的美妆账号被刚来的编辑给闹出了抄袭风波,被抄袭的博主一篇檄文直接把她们送上了抖音热榜,短视频部门现在还没有能顶事儿的负责人,公关稿这种东西只能她自己来。
听到父亲的话江白露大脑空白了一下,继而一股愤怒直冲天灵盖,她对着电话吼道:为啥都三天了才告诉我?报警了没有啊?
江白露很少用这种态度对父亲说话,电话里传来一阵沉默,接着父亲说:“报警了,还没消息。前两天不是跟她怄气吗,这会儿电话打不通了。”
打开出行软件,最早的飞机是明早六点。
还有六个小时,江白露从床上爬起来,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把已经写了三分之二的剧本完成,斟酌了几遍之后,把剧本发到账号项目群,用两条三十秒的语音把演员的表演、情绪和后期剪辑的基调讲清楚,又在群里拍了每个人两下,最后发了一段话说:“片子明天中午十一点之前要剪好发我,否则下了热榜咱们都要凉。”
安排好工作,江白露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王倩发了条微信:“家里突然有事,请假三天。”然后在钉钉上走了请假流程,当然这个流程对她来说只是走个过场,需要批准的人员也只有老板王倩一人。
行李收拾好之后,江白露才又拿起手机给男友时镇打了个电话,直到打了第二遍才打通,时镇的声音懒懒的,看样子是睡得正香,她简单和时镇说了说自己的情况。
“明早六点的飞机。”江白露最后说,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那,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江白露沉默了一小会儿,终于说:“不用了,你且先等等,我回来有话跟你说。”
在打出这个电话之前,江白露已经三天没和时镇联系了,这是和他在一起三年来最长的一次冷战。江白露一直以为自己对时镇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当时镇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到那种至亲至疏的凉意。
挂掉电话,江白露约了辆滴滴火速前往机场,司机是个和父亲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在江白露上车后就问了句:“有急事啊姑娘?”
江白露说:“是有点儿。”
司机没再说什么,但她明显感觉到车速变快了。安全快速地到达机场,江白露下车后在后台发了一个五十块钱的红包和一个好评,要是天下间所有的父亲都能这么靠谱就好了,江白露想。
02/知音
冬天的夜很漫长,直到登机,天还没有要亮的迹象,江白露也依旧没有等来时镇的一个慰问电话。
两年前她还只是一个用网上搜罗来的情感语录哄骗年轻女孩的公众号编辑的时候,就曾经以无比“清醒睿智”的心态写过:当一个男人问你要不要的时候,他的潜台词就是不想给,因为他想给就会直接给,甚至不管你想不想要直接强塞给你。当一个女人说不要的时候,她有可能是在跟你客套、撒娇、怄气,也有可能是真的不要,但总的来说,女人的情绪总是比男人复杂。
江白露此刻的情绪就很复杂,她也搞不清楚自己说的“不用了”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心态,如果她向他撒一声娇,示个弱,或许一切前嫌就能烟消云散吗?但她本来预期时镇的反应至少是:“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哪怕只是客套。
以他们的关系,最起码应该这样。
后座的小孩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大哭起来,孩子妈妈怎么哄都哄不好,周围都是些昏昏欲睡的赶路人,在这撕心裂肺又毫无停止迹象的哭声中,每个人都在或明显或含蓄地表达着不满。
江白露突然想起来,好像时镇就是从这件事上开始变化的,因为孩子。
两个月前,江白露和时镇同房时总是时不时出现不规律的出血,搞得每次两人好好的兴致都被搅扰大半,甚至不欢而散,时镇嘴上安慰着白露,身体上却显然对这件事开始有些排斥。
江白露抽时间挂了个妇科做了一通检查,中年女医生看着彩超单子淡淡地说了句:“巧囊啊这是。”
白露甚至都没听清医生说的是什么,只能又问了遍:“什么?”
“巧囊!巧克力囊肿,才2.2×2.4,不算大,最近打不打算要孩子?”医生手上飞快地打着字,嘴里说出来的话像是在和老熟人唠家常,但江白露还是一头雾水。
“不打算,大夫这到底是啥呢?怎么治啊?会死人吗?”
“没事儿,小事儿,就是现在它这个位置有点压迫你左侧的输卵管,可能会导致不孕。巧囊这玩意治不好,就算你做手术摘了,以后还会再长,而且手术对你身体伤害更大,所以最好就是吃药控制,能让它不再继续长大就不错了,等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再来决定要不要手术。”
江白露还想再问点什么,就被医生用一张长长的开药缴费单请了出来,去药房的路上,她在搜索软件上输入“巧克力囊肿”几个字,掠过置顶的几家来历不明的某系医院广告,总算看到了关于巧囊的详细介绍,顺带还解锁了一个新病:子宫内膜异位症。
江白露这才算是对这个毛病有了初步的了解:原来自己生了个不会死人的绝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毛病很有可能会一直伴随着她的后半生。想要让巧囊不再生长,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是不停怀孕,要么是不断避孕,而这个囊肿的位置也有可能让她一辈子不孕。
更搞笑的是,导致巧囊不断生长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根本找不到病因,也没有较为合适的根治方法,很多时候得这种病跟生活习惯、情绪、甚至脾气有关系,江白露回想了一下自己过往的生活,种种迹象表明,她会生这个毛病好像也并不意外。
江白露把生病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时镇,时镇心疼地抱着白露说:“一切总会有办法的。”这让白露心安了许多,毕竟她实在不愿意这三年的青春白白错付。
不久后两人就敲定在元旦安排双方父母见面商量订婚的时间。江白露来北京已有五年,她也想趁这个机会安排父母在北京好好玩一圈。至于病的问题,就像时镇说的,总能找到办法。
此后的许多天,江白露都在畅想着两家父母见面时的样子,她一边在网上给时镇父母挑选礼物,一边做着北京三日游的攻略,总之在时镇母亲电话打来之前,江白露对未来的一切都抱着美好的幻想。
时镇家在天津,十年前拆迁把一家人从小康之家直接拆成了小资产阶级。江白露去年就借着和时镇去天津旅游的机会去过他家,那时候她能感觉到,时镇母亲对身为公司高管的她并不满意,对身为一个东北工薪阶层家庭出身的她更不满意,但好在当时时镇坚定地站在她这边,母亲也拿他没有办法。
时镇母亲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江白露就有点不好的预感,尤其是当她开始罕见地对自己嘘寒问暖,然后开始试探性地问她的病情。
“医生也没有说一定就是不孕,是可以治的,阿姨,”江白露试图解释,甚至有点在向领导作报告的意思,临了又补充了一句“我还是很喜欢小孩的,主观上。”
“孩子,阿姨现在有个想法,说了你别不高兴,就是说呢,你现在就去医院跟医生问问,这个东西怎么治,马上就开始治,做手术啊还是做试管什么的,你和阿镇努努力,先把孩子怀上,只要怀上了你俩就立刻领证办婚礼,阿姨跟你保证,婚礼你想要啥样的阿姨都能满足你,彩礼什么也都好商量,但是阿姨也知道你这个孩子素质高,不是那狮子大开口的人。”
江白露一时语塞,好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刚开始她想象的结果无非两种,要么是劝分,要么是尚有一丝良心来安慰自己,但是她怎么都想不到对方会提出这样近乎无耻的想法。
时镇母亲以为她这是在发出什么无声的抗议,便又开始施压道:“十年前阿镇刚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卖了两套门市房给他在海淀买了套三居室,就为了将来孙子能有个北京户口,清华北大近水楼台,现在你跟我说你生不了,那我这一辈子图啥呢你告诉我?”
当时的江白露只觉得一阵恶寒像是顺着电话线直接击中她的脑子,对方的话她已经一句都听不进去,最后的理智告诉她赶快挂掉电话,否则她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无可挽回的话。
刚挂掉时镇母亲的电话,时镇的电话就过来了,江白露还没来得及开口,时镇就质问道:“你怎么能对长辈这么没礼貌呢?”
时镇说话时也没有多大的怒气,责难的语气中甚至还带着一丝温柔,也许他觉得用这种折中的态度就能像往常一样顺利地解决一切。
“所以你妈说的那些话,你是知道的呗?”
时镇沉默了半晌,之后缓缓开口道:“我也老大不小了,我爸妈确实比较着急抱孙子,希望你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谁来理解我的心情?我三十岁之前绝对不会生孩子的,前段时间刚因为转型的事和王倩吵了一架,现在我俩的关系早就不如以前了,我如果怀孕了,可能生完孩子回来,我的位置就被别人占了,到时候我怎么办,我在北京打拼五年的才换来现在的一切,你叫我怎么办?”
“到时候宝宝出生了你肯定不能立马上班吧?总得在家照看孩子吧,到时候你在家照顾孩子,我养你就行了,反正我又不是养不起。”
“所以时镇,你们全家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没怀上这个孩子,咱俩就完了对吧?”
“不会的,我相信现代医学,你肯定能怀上。”
如果不算江白露对时镇说的“你滚吧”三个字,时镇这句对现代医学的肯定应该是那天他们两个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的三天,江白露没有和时镇再说过话,时镇也没有主动找过她。
飞机随着雪花一起降落在太平机场,下飞机后扑面而来的是夹杂着尘土味的冷气,仿佛下一秒就能让鼻腔结冰。这再熟悉不过的,是让江白露感到无比心安的气息。
手机调回正常模式,江白露依旧没有收到时镇的任何消息。
回家这事江白露并没有事先告知父亲,所以当她拿着钥匙拧开家门的那一刻,父亲显然对她的出现并没有心理准备,他正坐在沙发上拿着一摞印着母亲照片的寻人启事仔细端详。
父亲抬起头与江白露四目相对时,眼中掠过一丝不安,又下意识地瞥向厨房,她有些奇怪。但当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端着一盘虎皮鸡蛋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江白露总算明白了父亲那一丝不安来自何处。
03/知音
“你咋回来了?”父亲率先开口。
“咋的我妈找着了?”江白露丝毫不想给父亲面子。
“没有啊,警察说在查她手机定位呢,但是现在她手机关机了找不着。”
“对啊,没找着呢,我自己妈丢了我还不能回来看看吗?但是咋感觉好像回来的不是时候呢。”江白露冷笑了一下。
空气中弥漫着尴尬和不安,总该有人出来辩解些什么,江白露想。
“这孩子你看看,”父亲脸上挂着尴尬而僵硬的笑,“这是你虹姨,忘了?咱家在阿城住平房的时候,她总来咱家,还给你带好吃的呢。”
“这么多年了,孩子大了指定记不住啦,是不是没吃早饭呢,我这刚好做饭了。”虹姨的语气中甚至带着一些理所当然,就像她认为现在自己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为别人的丈夫做早饭是一种理所当然一样。
这位虹姨她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只是此时此刻,时间地点人物似乎都以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方式排列,她显然无法立刻接受。
“这两天不是一直急着找你妈呢,你虹姨怕我上火,帮着做点吃的,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啥的。”
“快别在门口站着了,赶紧进屋呗。”虹姨放下盘子后,上前想接过白露的行李箱,她下意识躲开,鞋也没换,拖着行李进了自己的房间。
卧室床铺上换了一套灰白条纹四件套,多年没用的书桌上放着一堆理科高考复习资料,她打开衣柜,柜子里多了许多男式衣裤,书桌底下甚至放着一个篮球。
“那个姐夫啊,我下楼买点菜去,孩子好不容易回来,咱做点好吃的。”江白露一脸疑惑地走出房间时,虹姨像只黑夜里被手电筒照得无处遁形的老鼠一样,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这间令人窒息的房子。
“说吧,咋回事啊,鸠占鹊巢了呗?”江白露强忍着怒火,看着父亲点燃一根硬玉溪,试图用烟雾掩盖他的不安。
“这事儿真不怪我,你虹姨,他家男的死了,房子被要账的收走了,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这不是才来投奔咱家的吗?我当时可是说了帮不上啥忙,你妈非得在那逞能的,让她娘俩先在咱家过渡一下,找着合适的房子再搬出去。”
“那为啥成了我妈搬出去了?”
“那我哪知道呢?”父亲的烟燃尽了,也没有说出什么所以然来。
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江白露对这位虹姨依旧印象深刻。
04/知音
她念小学时,父亲在阿城的一家电力公司上班,虹姨一家和她家是前后院,虹姨身材瘦小,但脸蛋很漂亮,长得有点像黎姿,只可惜丈夫是个酒鬼,早上就着煎鸡蛋都能喝二两,喝多了就在炕上躺尸,通常情况下兜比脸干净。家里太穷,孩子出生两个月没有奶水喝,躺在炕上嗷嗷大叫,他都不会翻个身看一看的。
眼看着指望不上男人,虹姨刚出月子就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到市里摆摊卖袜子,夏天的时候还能背着孩子一起,冬天就只能把孩子送到江白露家照看。
江白露母亲可怜虹姨,但是冬天也正是澡堂子忙的时候,她就会把孩子带进澡堂,放在一个大号的洗衣盆里,扔上两个塑料鸭子让他自己玩,她就一个接着一个地给客人搓澡。
虹姨摆了一年多的摊,受不了母子分离的苦,也不好意思天天麻烦江白露母亲,就用摆摊加上借的钱在家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虹姨给女孩子做发型的手艺一般,所以更爱招揽一些男客人,几推子下去就能顺利完成任务,钱也好赚。
虹姨的孩子不满两岁时,周边关于她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许多人说她的理发店根本就是个幌子,实际上是开暗门子,不然靠她推头发挣的那点钱,哪够养活一家人的。
也有许多人说,住在周边的男人估计没有几个跟她没瓜葛的,于是周围的女人们开始对自己家的男人严加管教,一旦发现自家男人去虹姨那里理发,绝对会大闹一场。江白露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她在家里也听到过母亲警告父亲不许去虹姨那里理发。
后来父亲经人介绍调岗到了南岗,一家人就卖掉了阿城的房子举家搬迁在南岗定居,和虹姨家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十几年过去了,虹姨还是像以前一样瘦弱,四肢纤细,但是脸上的皱纹证明这些年她显然过得并不好。
父亲解释不清楚母亲出走的原因,两人正僵持着,江白露看到门把手被拧动,一个眉眼清秀,高高瘦瘦的男孩走了进来,他敞怀穿着件黑色长款羽绒服,羽绒服里面套着三中的校服,想必外面的雪下得不小,落在他头上的雪还没有化净。
男孩看到江白露,本就十分落寞的脸变得更加阴沉,江白露知道,这就是占了自己老巢的那只小鸠崽子了。男孩站在原地没有说话,江白露父亲赶紧介绍道:“这是你虹姨的儿子,田川。这不是来三中复读嘛,所以才在这儿借住的。”
“哦,那得在这住了两三个月了吧?你们这找房子效率不高啊,咋的,哈尔滨没人出租房子了?”白露说完之后有点后悔,感觉自己是在对一个孩子无能狂怒。
田川看了江白露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进白露卧室,接着是一顿翻箱倒柜的声音。他极其快速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抱着篮球直奔大门,老江连忙上前阻拦。
“江叔你不用拦我了,我自己在外面找了个家教的活儿,包住,这段时间我跟我妈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等我以后挣钱了,一定报答你们一家。”田川说着挣开老江的手,老江赶紧给拨通虹姨的电话,然后死死拉住田川说:“等你妈回来再说!”
“那我妈什么时候回来啊?”江白露质问道。(未完待续,明天继续更新。)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知音
知音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