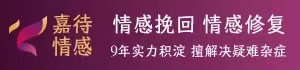17岁湘妹子不顾父亲反对报名援疆,后来的故事太感人...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感召下,先后共有八千多名湘女挥别故土,踏上援疆之路。她们扎根边疆,屯田垦荒,成为荒原上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女医生、女教师、女农技师,改写了中国历代屯垦事业“一代而终”的历史,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
70多年后,当年风华正茂的湘女,很多已不在人世,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湖南省妇联宣传部、省妇女学研究会、今日女报/凤网全媒体联合启动了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抢救性记录“八千湘女”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敢于担当的意志品格、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我们希望完整记录并大力弘扬当年八千湘女的奉献故事,并激励新时代湘女更好地传承老一代湘女精神,将新疆、湖南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本期,我们推出《湘疆绽芳华——八千湘女口述史》系列报道第一篇《新疆,留下的是我永不枯竭的青春》。


【湘女档案】
湘女刘布诚,1933年出生,1950年2月进疆,在南疆军区第十二医院传染科工作,1970年转业回到长沙。目前居于长沙。

新疆,留下的是我永不枯竭的青春
口述/刘布诚 文/方雪梅
1950年秋天,岳麓山的枫叶红了,湘江两岸,氤氲着火一般的激情。这是全国刚解放的第一年,在战火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此时,重振旧山河、建设国家的热潮,仿若摧枯拉朽的飓风,席卷各行各业。
这一年,我刚满17岁,在长沙湘雅护理学校读书,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与动荡日子,解放后的新气象,让我与许多青年学生,都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内心的热血也被点燃,嗤嗤地沸腾起来。我们都急切地希望投身于建设新天地的时代洪流。
时令正是9月,一个消息,像划过天空的闪电,让我们班几个正在湘雅医院实习的女同学兴奋不已。原来,报纸上刊发了新疆军区技术人员招聘团到长沙招人的新闻。我和闺蜜罗蕴华等五个女生,兴高采烈跑到营盘街去报了名,且很快被批准入疆。

▲当年新疆招聘团在《新湖南》报上刊登的招兵公告
听说我要到千山万水外的地方去,外祖父十分不舍。是啊,他唯一的女儿生病去世时,把5岁的我和3岁的妹妹托付给他,从此我们在外祖父的膝下长大。相依为命的外孙女,一个人远走天涯,他哪里舍得?而父亲对我的决定,十分生气,眼看我这个家里的大女儿可以工作养家了,却指望不上了。父亲是黄埔军校5期的,我小时候,他在抗日前线打仗,日本投降后,他回到长沙再婚,生了7个弟妹。父亲希望我留在长沙工作,帮衬家里。其实父亲不知道,早在周南中学读书时,我就接触过共产党人的宣传小册子,学会了唱“山那边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就做工呀,没人为奴做牛羊……”的歌曲。受进步思想影响,我还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新中国成立了,我如火如荼生长的青春理想,有了开花结果的土壤,参军、奔赴边疆去建设国家,就是我最坚定的选择。家人的不舍,父亲的雷霆之怒,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9月中旬的一天,我与同学们一起,告别长沙,坐上了西行的绿皮火车,向着未知的远方进发。一路上,大家像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谈笑、唱歌。火车到达西安,稍事休整后,我们20多个“湖南娃”,和行李一起,挤在一辆老旧的敞篷大卡车中,沿着险峻的土路翻山越岭,颠簸着驶向兰州。车过六盘山,窄窄的盘山小路,像扭曲的细蛇,挂在悬崖峭壁上。我两手抓着车篷栏杆,双脚悬在车外,任耳畔山风呜鸣,脚下深渊百丈,毫不畏惧。从山顶看后面山下盘旋而上的车辆,如挂在绝壁上,每前行一米,都险象丛生。由于交通条件差,进疆的汽车陈旧,车队沿途抛锚和出现车祸的状况时有发生;加上西北土匪残部出没,有的人还没有踏上新疆的土地,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时的新疆,山长水远,在人们印象里,是历代罪犯充军的荒僻边塞,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但这阻挡不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的脚步。
旧中国文化落后,解放初期,学有专长的人才很稀罕,新疆尤其奇缺。所以,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奔赴边疆,可谓雪中送炭。当然,17岁是一个少女多梦的年龄,对浩瀚的戈壁,广袤的草原,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以及蓝天、白云和成群的牛羊,我也充满了憧憬。但最主要的还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革命激情和对军人崇高形象的倾慕,坚定了我奔赴边疆的信念。

▲八千湘女进疆路线手绘图
到达兰州后,部队的军服发下来了。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装,姑娘们兴奋得又叫又唱,歌声不绝,洒了一路。过了兰州,进疆之路,越来越荒凉,且一会儿冰雹,一会儿雨雪。人烟稀少处,只看得到左公柳的树根残迹,看得到戈壁滩的石头和一望无际、苍茫的地平线。充满青春活力的我们,看到祖国的塞外美景,格外高兴,时而为戈壁尽头出现的壮观的海市蜃楼欢呼,时而又为那偶见的沙漠中的绿洲而激动。当汽车进入新疆地界时,巍然竖立的一块大石碑出现在眼前,上面刻着醒目的大字:“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大家顿时心潮澎湃,一阵雀跃。这意味着,新疆到了!从长沙暑气未退尽的初秋出发,经过四十多天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旅程,我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当时还称迪化)!迎接我们的是漫天飞舞的大雪,还有部队给我们准备的温暖的毡靴和没有布面的羊皮大衣。
乌鲁木齐街景,萧条而贫穷。满眼是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土砖泥巴平房。几乎没有店铺,人口少,物质也匮乏。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更没有火车、公交车。严寒和少雨,是气候常态。看到一穷二白的城市,我感到肩上担负的建设新疆的责任,是沉甸甸的。
就这样,在天山脚下,我们开始了人生与事业上的另一次长征。

▲刘布诚(左)和一起进疆的湘女合影
几天后,五个女同学都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医院”。
报到的第一天,听说我们会被安排去口腔科,大家十分诧异。院长问:“你们不是镶牙的吗?”姑娘们面面相觑,不知就里。原来,头一天,招聘团的一个同志,兴致勃勃地给院长介绍:“我给你们从长沙找来的,都是镶牙的……”我们一听,乐了:“我们是湘雅的,不是镶牙的!”大家笑成一团。姑娘们被分到了各个科室,后来都成了医院的骨干。我则分配在内科。
医院旧而破,只有几排土坯泥巴房,几棵叫不出名字的树,光秃秃地向四周张开枝丫。这是接收国民党的军医院,条件非常简陋,药品也十分紧缺。病员很多是原来留下的起义人员,体质普遍较差。内科以肺结核病人居多,因为当时链霉素要靠进口,没有特效药医治,重症病人死亡率较高,有时一晚上死几个。肺结核有传染性,医院又没有有效的隔离设备,医护人员全靠着年轻,体质好,超负荷地完成任务,谁也没有退缩。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像勤劳的小蜜蜂,早早地起床,背着爬犁去郊外积肥拾粪,教当地人种菜、施肥。回来后就爬上房顶扫雪,以防屋顶被厚厚的积雪压垮,然后才吃早餐,餐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医疗工作,晚上政治学习;上晚班的人,白天也有同样的劳动任务。大家工作起来,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个个争先恐后,干劲冲天。新疆当时的农业很落后,工业基本是从零开始。部队教会了当地农民很多农业技术。大批军人热火朝天地参加了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等工厂的兴建。我还记得当时有人在动员会上倡议,说:“我们每人少领一顶棉帽,少领一件毛大衣,就可以多盖一个工厂……” 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我们,发出了“不要帽子!不要大衣!”的回应。大家的军装,缝缝补补,直到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舍得换。有一次我的宿舍失火,烧坏了盖在被子上的棉衣,所幸人没有烧伤,但院里给我补发了一件新棉衣,穿在身上,我感觉自己搞了特殊化,心里忐忑不安。
气候苦寒和饮食不习惯,对我们这些南方人,也是一种考验。每到冬天,我们不少人的耳朵,手脚就长满冻疮,肿得像馒头;在吃的方面,常常是高粱包谷换着来。南方人对白面尚不习惯,对杂粮就难咽下了。但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劳动任务,我和几位女同学,会逼着自己填饱肚子。因气候干燥,我经常扁桃体发炎,喉咙疼得像要冒烟,粗粮咽不下,就喝点面糊糊。在艰苦的岁月,我们都努力让自己适应环境,锻炼坚强的意志。与我同来的四个姑娘,后来都成了医院的骨干,用行动谱写了无悔的青春之歌。

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接踵而来,大家壮怀激烈,抱定“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生在边疆,埋在边疆”的想法。花样年华的男女,怀着同样的理想,在遥远的边疆,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孕育了许多美好的爱情故事。
我的老同学、好闺蜜罗蕴华,是个活泼可爱的长沙女孩,军帽下,挂着两条齐肩的麻花辫,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很快她就被月老的红线给套住了,对象是同一个医院的军医。她与我分享自己爱情的甜蜜,并且热心地鼓励我大胆寻找幸福。看看身边,有的姑娘嫁给了志同道合的心上人,有的女孩正在享受恋爱的幸福。我身边的每一对恋人,秉承的都是新时代的自由恋爱思想。那种封建家长式的包办婚姻和拉郎配的旧习俗,被大家弃之如草芥。
1951年,一个来自浙江临海的小伙子,闯进了我心里。
他叫王汉云,是我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虽然只比我大5岁,却是一个“老革命”。他以前在浙江的医学院读书,是文娱活跃分子,经常给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帮忙,后来加入了游击队金萧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号召,于1950年2月参军入疆。单单瘦瘦的他,相貌堂堂,个子也高,不光业务学习勤奋,而且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是医院的团支部委员。他恰好与罗蕴华的对象住在一间宿舍。工作与生活中打交道多了,我们很谈得来。罗蕴华和男友也欣赏王汉云的人品,极力促成我与他走近。1951年,我们很自然地相恋了。他性格好,有江浙人特有的柔和,很体贴人。见我冬天手脚总生冻疮,他一个拿手术刀的男人,居然亲自动手给我织了双红色的毛线手套。看到匀称的针法,和分叉的五个小指套,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感受到了久违的家人般的温暖。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53年元旦,我们参加了部队组织的集体婚礼。一场革命化的晚会上,四对年轻人结为夫妻,开始了甘苦与共的新生活。在新疆的土坯房、地窝子里,大家把艰苦的日子,过出了花好月圆的幸福。现在回头看,觉得那时条件艰苦,但年轻时的我们,以苦为荣,将爱情之花,根植在天山脚下,且深感骄傲。我们五人中的一位姑娘,就硬是将她在清华大学刚毕业的未婚夫动员到了乌鲁木齐。直到退休,他们还留在新疆大学。

▲在田间地头吃饭(资料图)
婚后不久,汉云接到了命令,前往南疆工作,目的地是喀什的“解放军十二医院”(原称“二军医院”),我这个内科护士长也随丈夫一起调过去。“二军医院”的前身,其实就是南泥湾部队三五九旅的卫生队,严格意义上讲,还不算正规医院。因为医护人员奇缺,我们被作为支援力量南调。
1953年3月,天上脚下,依然寒意深重。坐在军用卡车里,我们一路颠簸,向着1400多公里外的陌生土地开拔。一路上,人迹寥寥,只有戈壁、沙漠、草地和无穷无尽的雪山,将大自然的壮美,展现得如诗如画。可已经怀有3个多月身孕的我,无心欣赏美景, 晕车和妊娠反应叠加,让我如翻江倒海般呕吐不止。足足颠簸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到达了人生地不熟的喀什。
来到新单位,我们马不停蹄投入工作。当时医院不成规模,也没人熟悉业务管理,一切都待重启炉灶。王汉云去后,开办了一个“医训队”,我则负责教护士们怎么执行医嘱,怎么交接班,怎么照顾病人……
三五九旅的光荣传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医院也是如此,生产常抓不懈。大家开垦了1000多亩地的农场,种菜、做豆腐,养牲口,一切都自己动手。这天,我正在地头休息,组长领着一个满面愁容的维吾尔族大叔,急急忙忙向我跑来。原来大叔的妻子生孩子,发作已好几天了,却一直没有生下来。产妇早已痛苦不堪,很可能出现母子性命不保的危险。危急关头,大叔想到了向解放军求救!在他心里,给予了当地老百姓很多帮助的解放军是值得信任的。
当时,少数民族的风俗,不容许男人助产接生,而农场只有我一个女医护人员。麻烦的是,我不是产科医生,怎能担此重任?万一无法应对复杂情况,该怎么办?看到大叔焦急和期待的眼神,我知道人命关天,时间不允许我再犹豫。就算赶着鸭上架,也要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我拿了卫生药箱,就跟着大叔奔向他家。
看到产妇当时的状况,我大吃一惊:这个高龄产妇躺在土炕上,炕上铺着沙。从她身体里流出的血和羊水,已经将沙子染红。我初步检查胎位还是正常的,但产妇已极度衰竭,呻吟也变得微弱。一了解,大叔情急之下,采取了不正确的土法助产手段,还准备让妻子趴到马背上,挥鞭抽马,让奔跑的马匹,将孩子颠下来。听说这些,我倒抽一口凉气,告诉他千万不能这样做;并嘱咐他赶快去给妻子做碗鸡蛋羹,让产妇恢复体力。待产妇面色转红些,我一面安慰她,教她深呼吸,一面伸手帮助她加强宫缩。好一阵紧张的忙碌后,一个漂亮的大胖小子,来到了人世。
当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我仿佛听到了一首最动人的歌曲,吊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喜悦的欢呼,大叔和他的家人们,兴奋得大叫:“谢谢解放军!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
这件事,让年轻的我,高兴了很久。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当年的胖小子现在应该有四十岁了,不知他在干什么?一定成家立业了吧?新疆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他的生活也很幸福。

▲本文作者方雪梅(左)在采访病床上的刘布诚
1953年底,20岁的我,在漫天大雪时生下了女儿。初为父母,我和丈夫十分高兴,给她取名叫“沙婴”,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生下的婴儿,小名叫沙沙。怀这个孩子时,我突然特别想吃长沙的仔油姜和“猫乳豆腐”,可关山迢迢,哪里去找?丈夫见我呕吐难耐,只好到街上的药店买点干姜给我止吐。孩子出生后,我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就经常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或者放床上,或者把她绑在椅子上。那时,我们医院还没有幼儿园,也很难找到保姆。我与汉云都是医院的骨干,工作离不开。将女儿独自留在家,她常常哭得声嘶力竭,哭累了就自己趴下睡着了。我只能在工作中途,抽空跑回家看看。每次下班,看到她小脸蛋上的眼泪,我是又心疼,又内疚。
有一天上午,风狂雪急。我丈夫上班忘了带钢笔,没法给人写病历,就回家去拿。远远看见家门外,白皑皑的积雪地里有一团醒目的红色,他还以为是哪个路人,不小心掉了什么物品。待走近,才心疼地发现,竟然是一岁多的女儿,光着屁股,从家里的床上爬到门外来了。不知她在雪地里趴了多久,全身冻得冰凉。汉云大步冲上去,赶紧抱起孩子,回到室内,流着泪用热毛巾给她擦干身体。他不敢想象,如果自己中途没有回去拿笔,孩子肯定有性命之虞,不说冻死,也会冻成残疾。我们想想都后怕,也十分愧疚,不久就想方设法请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大姐来照顾沙沙。
1955年春天,我给沙沙添了个弟弟,取名叫晓亚。这时候,我们医院已经有了全托的幼儿园,孩子们终于有人照顾了。我和丈夫感觉踏实了许多,心想从此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就在这时,厄运劈头盖脑向我们扑来:一岁多的晓亚,出麻疹住进了我们医院小儿科。孩子出院时,他父亲正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而我恰好在值班,无法离岗。于是,我请幼儿园老师把晓亚接回幼儿园住。因为天寒地冻,保育员怕他冷,把他的小床,移放到火炉旁。夜深人静时,孩子的小被子掉到炉子上,燃烧起来……待我再见到晓亚,心痛得缩成一团:孩子两腿自膝盖以下,几乎烧成黑炭,脚趾头一碰就一个个掉了。他痛得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满嘴鲜血,陷入深度休克。眼见孩子生存希望渺茫,我根本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全力以赴抢救孩子,并就孩子后续治疗予了强力支持,派专人陪我和孩子到北京协和医院求医。在北京住了半年院,又转到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经过二十多次手术,孩子的命保住了,却失去了脚掌和脚趾头,落下了终生残疾。想到他小小年纪,就必须接受以双拐支撑未来人生的命运,我的泪水无数次打湿了午夜的枕头。我请医生割下我身上的皮肤,移植给孩子,却无法冲淡我的愧疚和刻骨铭心的痛苦。我觉得自己是个好军人,却不是个尽职尽责的好母亲。
在喀什工作十七个春秋,我和家人一起,体味了边地生活的沉苦,也感受了生命力激情的光照。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湘女,为新疆的建设发展,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背后,是荣光也是苦难,是坚韧也是牺牲。每当看到横亘的天山南脉,耸立的喀喇昆仑,我就觉得那是一代人雄风凛凛的坚强脊梁。我也始终无悔将青春的万丈豪情寄放在新疆大地。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转眼,我已经入疆20年了。人到中年后,乡愁重了。遥远的东部故乡,常常会在我们心海卷起波澜。家乡的村酿野蔬,林泉桃李,以及微雨漂舟,都会在梦里出现。由于晓亚移植到脚上的皮肤经常出现破溃、化脓,学习成绩很好的他,常常被同学背着上学、上厕所……他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便,提醒我必须为他的未来作打算。考虑到儿子成年后内地的就业机会相对会多些,我选择复员,带着一双儿女回长沙。丈夫因为是医院无法或缺的业务人才,服从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喀什工作,坚守我们支边的初心。
回到长沙后,来不及欣赏故乡天空的云朵,也顾不上感叹湘江两岸天翻地覆之变。我拿着儿子的一堆奖状,找到长沙市一中。学业优秀的晓亚,很快被接受入学了。他爱好音乐,学习识五线谱、弹钢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了中国音乐学院,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入学。命运再次对他张牙舞爪,他还是没有被击败,反而更加努力,后来到电大学习,进入民政系统的旭华仪表厂行政科工作。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被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二十多岁时,他烧伤的双腿因为反复溃破而被截肢,但他以坚强、乐观和才情,赢得了163军医院一位美丽女护士的心,成为这位女军人的丈夫。我女儿沙沙也被组织照顾,进了第二机床厂;两个孩子是被边地大漠的风霜养大的,能吃苦耐劳,都在单位入了党。我呢,也被安排到二轻工业局系统,先后在模具厂和钟表厂的医务室工作,直到退休。
1983年,我的丈夫也告别工作了30年的新疆,调来长沙,任长沙市第一医院院长。我们结束了13年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生活,全家团聚在湘江边,岳麓山下。
退休后,我和丈夫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他热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我上老年大学,学写诗词,还在湘雅老年大学当了三年班主任。我们金婚那天,住在附近的儿子女儿,带着他们的孩子回来祝贺,还鼓动我与老伴补拍了一张婚纱照。当年,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结为伉俪,满心想的是多为边疆建设出力,连一张像样的结婚照都没顾得上拍。穿上洁白的婚纱和笔挺的西装,我们看着彼此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仿佛回到了充满激情的青春年岁,感觉生命中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无数次,我们在夕阳下散步,总会回忆在边陲生活的点点滴滴;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会不约而同地关心喀什和乌鲁木齐的冷暖。我们人离开了,魂却还牵系着帕米尔高原、古玛塔格山、喀什噶尔河,牵系着留在那里的老战友们。
现在,老伴因病离开我已有十四个年头。当年一起远赴天山的五个女同学,也只有两个人健在了。每当我翻看旧日的照片,就忍不住想告诉汉云和“姑娘们”:我和孩子后来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故地重游,看到当年荒僻落后的地方,都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景点,高速公路将它们像珍珠般串起来,高楼大厦取代了地窝子和土坯房……当年我们种下的杏树、石榴、桑树、梧桐,正在雪山下,郁郁葱葱。作为年近耄耋的老人,能看到国家一天天走向富强,百姓生活喜乐,是我最大的福气。我们这批湘女,支边戍边,不就是就是希望这片江山,能长久国泰民安吗?
从万里边疆的军医院到南国故乡的工厂,20年从军,13年军嫂,我的人生轨迹,是一道圆满而美好的彩虹,而作为湘女,我们永不枯竭的青春,与远方的格桑花一起,为养育自己的土地尽力芬芳过,就无怨无悔。

- END -
采访手记:
住在我家楼下的刘娭毑
2022年4月16日,长沙雨凉云浓,气温低落。我敲开了5楼一户邻居的家门。
没想到这次的采访对象刘布诚老人,居然是我楼下的近邻。开门的圆脸女子,是照顾刘娭毑的护工。她指了指里面的主卧,说:听说你来采访,娭毑早就在等着呢。
主卧室靠北,一个皮肤瓷白,身形清瘦的老太太斜靠在床头。她满脸笑意,有种天然的暖心气场。89岁了,居然见不到几丝白发。让我开心的是,提起在天山下的往昔,她的话,就如叶尔恙河,源源不绝,细波巨浪,潺潺而起。
采访前,最担心遇到金口难开的人,没想到眼前的老太太,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提到在新疆的那些年,她谈兴高涨,让护工从柜子里拿出几本影集,里面有许多黑白照片,都是湘女们当年参军时英姿飒爽的戎装照。她一张张指认照片上的战友,脸上满是温暖神情,思绪沉浸到往事深处。她说:“人上年纪了,就喜欢回忆年轻时代。我经常想,我们这批湘女,不计个人利益,离乡背井去边疆,都是顺应时势召唤。那个时候,人们思想干净,一心为国家着想。作为平凡人,我不后悔在边疆呆了20年。吃苦受累,做栽树的前人,给后人留一片荫凉,我觉得很有意义。”
刘娭毑身边的置物柜上,摆放着她与丈夫金婚时拍的婚纱照。耄耋之年,老夫老妻才穿上婚礼服装,以纪念一份历经风雨后的幸福与忠贞之爱。她告诉我,自老伴2008年肺癌离世后,自己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就住到长沙安华养老院去了。入住的大部分老人,都是穿过绿军装的。院长也是转业军人,有军旅情结,对养老院的抗日老兵,一切费用全免。他创办养老院的初衷就是让老兵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刘娭毑与老军人们住在一起过得很开心。大家聊天,下棋,唱歌,回忆从军的趣事,十分惬意。不幸的是,几个月前,她不小心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从医院出来后,就回家了。现在很少出门,儿女们给她请了这个护工,照顾卧床养伤的她。
听说我做了多年编辑工作,她十分兴奋,吩咐圆脸护工,从抽屉里翻出自己写的诗文,其中有装订成册的《霜枫晚唱》《霜枫晚唱续集》以及《刘布诚诗词新作》。她翻出一张小纸片说,这首新写的诗,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岂能往事逝如烟,军旅生涯忆万千。倘若时光穿隧道,青春成熟赛当年。屯垦戍边不顾身,芙蓉绽放战沙尘。风霜雨雪等闲度,誓当高原追梦人。”
她谦虚地说,自己还是学写阶段,写得不完美。可从她的字里行间,我读到的是一代屯垦戍边人的家国深情。其实,她与一代湘女,早就在天山下,写出了最好的诗句。
三个小时后,我起身告辞,刘娭毑欠了欠身体,笑着挥手:有空多来聊天哦,跟你讲新疆的故事,我蛮高兴的。
作者简介:方雪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长沙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编辑:菜菜 、伊人
审核:陈寒冰
“晒美好 向未来”视频(图片)大赛
火热进行中……
点击图片,一起晒美好吧!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今日女报
今日女报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